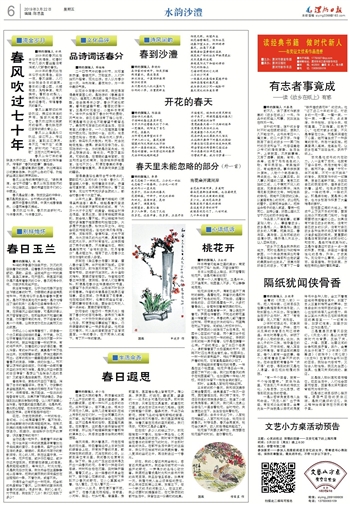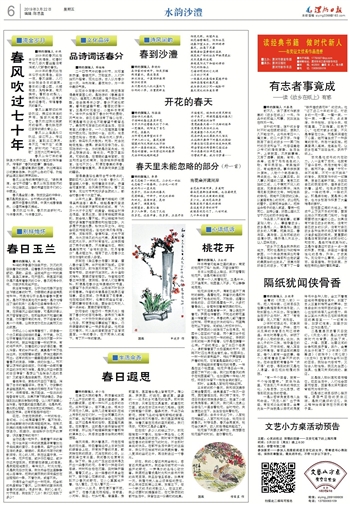■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在单位大院的墙角,我惊喜地发现了几丛开放的野花,蓝色的婆婆纳,黄色的酢浆草,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白花。三种花皆小,若不凑上去,根本分不清花分几瓣。当我几近匍匐地趴在地上用手机拍它们时,一位女同事见状大为不解,她不能理解我的举动。在她眼里,这不过是卑微的俗物,甚至毫无美感。在我看来,这却是大自然留给城市的诗意,所以她不能理解我竟怀着那样的谦卑之心,来感谢这春日给我的特别馈赠。
每天清晨,我沐着温风,行走在橘色的阳光里,呼吸着路边柳上日渐加深的绿意去上班,所有关于春的讯息,都流转在我的眼波,沉淀在我的心田。从家到单位有三里,我的春光也便有三里。除了柳,路上的广玉兰还没来得及开出一朵春天的花,冬青仍一抹老旧的苍绿,柿树和白杨在沉睡,栾树睁开睡眼,看看又闭上。这一路春的讯息全在树下,若你留心观察的话,会在树下寻到不少春天的野花,它小心翼翼地开着,怕人看见,又怕人看不见……
幼时一入三月,野花便不管不顾,全开了,在春风里无限招摇。田野里、小河畔、路边、村头村尾、巷道里、房前屋后,甚至墙头檐上皆有花开。蒲公英、荠荠菜、打碗花、酢浆草、婆婆纳……三月的乡村是花的世界。那时我们很穷,只有压在文具盒底,或塞在枕芯里,或夹在日记本中的几毛钱。但我们拥有整个田野、整条河流、千朵万朵野花,拥有飞鸟的鸣唱和野鸭的絮语,拥有全部清风和春阳。我们甚至拥有翅膀,伴着风筝在无垠的蓝天翱翔。我们很穷,可同时又是多么富有。
现在呢?多少人的钱以万计,却无暇摘取一片春光,捡拾一声鸟鸣,心灵的贫瘠是真正的贫穷。我时常怀想起那些在春日的田野放飞的时光,怀念那时单纯的快乐。在都市生活中奔忙的这些年,我似乎已被城市的洪流裹挟着,卷入更深的幽闭之中,再没射进过一寸春光。
好在,我的心智还未完全钝化,感官还未完全麻木。我还会为城市的一朵盛开的野花,一声偶尔的鸟鸣心动欢喜。我愿把这看成是时光和大自然对我的共同恩赐,我且珍惜且感激。如果有一天,我履行完人生必须承担的责任,那么我将回到南山之南,东篱之下,做一个耕风钓月的闲散之人。在这之前,我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在忙碌烦琐的都市生活中,保留住这一份最初的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