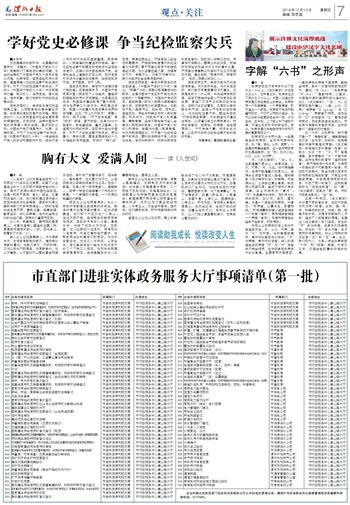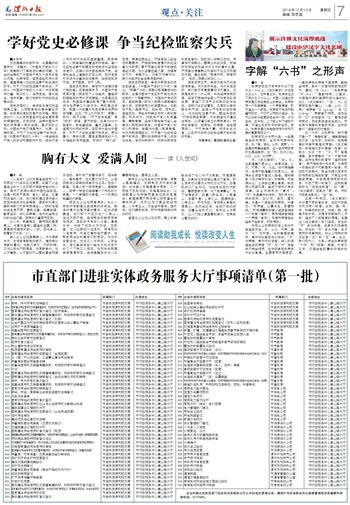■张 晗
形声字在现代常用字中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说文解字》中达百分之七十,在甲骨文中,形声字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国人创造出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奇迹。形声字用一个形旁表意,一个声旁表音,即可造出一个新字。形声字不拘泥于数量和形式,不仅可以两部分组合,也可以三部分或更多组合为一字,分为左右、左中右、上下或上中下结构不等,可造出无穷无尽的新生字。因此,形声字是汉字能够流传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声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纯的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构成,如“祺,吉也。从示,其声”;一类是形声兼会意字,这一类形声字同时也是会意字,如“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
河,《说文解字》:“ 。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从水,可声。”河,水名。古代特指黄河,发源于敦煌塞外的昆仑山,自源头出流经千里注入渤海。据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的解释,河自源头出,上游穿过黄土高原,挟泥带沙流至平原,造成下游河水常年浑黄,由此河被称为“黄河”。“河”本是黄河的专称,后引申为水流的统称,如沙河、淮河、澧河等。河是一个典型的形声字。许慎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即根据事物的意义或类型确定一个形旁(意符),再根据读音确定一个声旁(音符)。形旁和声旁组合起来产生新字,即形声字。
依照以上形声字的定义来分析其造字方法。河,从水、可声,其中“水”为形旁,也称意旁或意符,表示河的意思与水相关;“可”为声旁,表示河的读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声旁“可”与“河”读音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在形声字中比比皆是。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形声字的声旁不强调声、韵完全相同,其中一方面相同或相近即可,譬如“河(hé)”与其声旁“可(kě)”是韵相同;二是古、今语音本身的差异和变化造成的。如江,《说文解字》:“ ,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从水,工声。”其声旁“工(gōng)”与“江(jiāng)”声韵皆不相同,但在当时“江”的读音与“工”是相近或相同的,后世其读音发生变化,而由其作偏旁的字音却未变,这种现象叫“语音的历时演变”。
谈“六书”之形声字,就不得不提一下“偏旁部首”。偏旁是指组成汉字(合体字)的部件,包括表意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说文解字》部首指汉字中表意(形旁)的部分,比如“河”,“水、可”皆是偏旁,其中表意的“水”才能作部首。这种性质的部首称“造字法部首”,其严格按照六书体系,只有同一形旁的字才可隶属同一部首;而在现代字典中,完全依据汉字字形的相同部位确定部首,不再区分形旁或声旁,许多具有相同部件的字,列在了同一部首下,这种部首被称为“检字法部首”,如“甥”,《说文解字》将其归“男”部,而现代字典将其归入“生”部。
还有一种情况,《说文解字》中分属不同部首的字,在现代字典中列为同一部首。如肤、腿、胀、肿、胖等肉部的字,与朗、期、朔等月部的字,依据字形都被列入月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但通过《说文解字》我们发现,字左的“月”多为肉旁,与身体肌肉等相关;字右的“月”多为月旁,与月亮和时间等相关。与以上相同的情况还有“王”和“玉”等。总之,我们现代人,尤其小学生如果熟悉“六书”和“部首”原理,对学习汉字、汉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