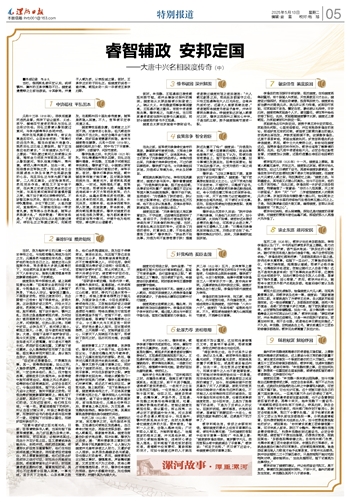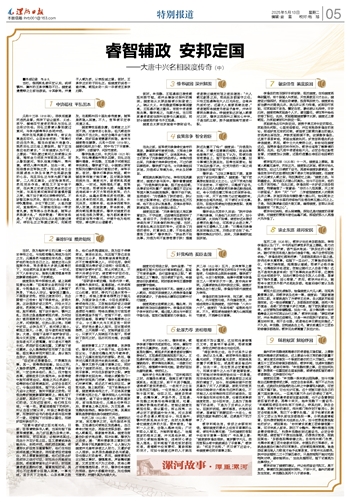■本报记者 陈全义
当初,淮西叛乱被平定以后,统领镇州、冀州的王承宗震恐不已。裴度遂遣善辩之士前往游说,令其献地,并遣子入朝为质,以表投诚之意。彼时,王承宗正求助于田弘正。经裴度的说客一番劝解,朝廷未动一兵一卒便使王承宗归降。
1中流砥柱 平乱固本
元和十三年(818年),因李师道屡次违抗圣意,宪宗下诏让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使的军队与田弘正会师讨伐他。田弘正奏请从黎阳渡过黄河,与李光颜等军队协同并进。
宪宗在延英殿召集宰相,商议此事是否可行。众臣纷纷进言:“军事行动远在外地,理当由前线大将裁夺。既然田弘正已经上奏陈明,陛下应当答应他的请求。”只有裴度认为不可,上奏说:“军队渡过黄河之后便难以后退,唯有全力进攻方有取胜之机。若从黎阳渡河,军队刚离开魏州、博州境,便进入滑州地界。如此一来,朝廷徒增供应军饷之劳,而出征将士会因顾虑战火殃及本境产生观望犹豫的心态。况且田弘正与李光颜不够果断,二人相互猜忌,必定贻误军机。然而用兵作战,朝廷又不宜中途干预,在决策之初便应拟定周全的应对方案。与其在黄河南岸采取谨慎持重之策,倒不如于黄河北岸等待时机。不妨暂且秣马厉兵,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待秋霜降临、水位下降之时,从杨刘渡河,直捣郓州。只要能在阳谷一带安营扎寨,官军势头自然强盛,贼军必然阵脚大乱。”宪宗赞道:“卿所言极是。”于是下诏让田弘正从杨刘渡过黄河。待田弘正之军渡过黄河,向南进发,在距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寨,贼军果然陷入困境。不久,官军便平定李师道之乱。
裴度秉性坚毅执着,在朝堂之上不屈不挠,对皇帝忠心耿耿。但凡朝政存在疏失不当之处,他定会竭尽全力直言进谏。因奸臣皇甫镈屡次构陷,皇帝与裴度渐生嫌隙。元和十四年(819年),裴度任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穆宗登基之后,长庆元年(821年)秋,张弘靖遭幽州军队囚禁,田弘正在镇州遇害,朱克融、王廷凑于河朔地区举兵叛乱。穆宗遂下诏,令裴度以原有官职充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率军平叛。彼时,穆宗行事骄纵荒诞,朝中辅政宰相皆才能平庸,且对复杂局势把控失当、调度无方,致使叛乱再度爆发。一时间,局势混乱不堪,官军士气低迷。即便有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统率十多万大军进攻叛军,仍久战无功,丝毫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裴度从受命的那天起,就招募士兵、补充兵员,无暇休息。他亲率西部军队深入敌境,攻城拔寨,斩杀叛将,频频向朝廷奏报捷讯。穆宗对裴度的忠诚与担当极为赞赏,每月都派遣宫中使臣前往军中慰问,并晋升他为检校司空,兼任押北山诸蕃使。
2奏除奸佞 整肃朝纲
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元稹一心谋求宰相之位,与知枢密魏弘简结为生死之交。元稹虽然与裴度没有仇怨,但嫉妒他的地位在自己之上。裴度正在山东指挥作战,军务奏报大多被元稹等拦下,无法顺利呈至皇帝面前。一时间,天下人纷纷议论,皆称元稹凭借皇帝恩宠肆意迷惑圣听、干扰朝政。
裴度身处军中深感忧虑,遂上疏朝廷奏论此事:“臣闻君主圣明则臣子忠直。今既逢圣主,愿为直臣,上酬陛下殊恩,下绝众人非议,誓除国之蠹虫,不顾身家安危。若臣之建言可行,岂会顾惜一己性命?陛下恭承帝业,宏图大展,正欲荡涤奸佞之邪气,开创太平之盛世。然叛贼兴乱,震动山东;奸臣勾结,败坏朝纲。陛下欲平幽州、镇州之乱,当务之急是整肃朝廷内部。为何如此?盖因祸患有大小之别,议事有先后之序。河朔叛贼,仅扰山东之地;而朝中奸臣,必殃及天下。故河朔之祸小,朝廷之祸大。小患,臣与诸武将定能剿除;大患,非陛下圣断不能铲除奸臣。现今文武百官,朝廷内外众多官员,有良知者无不义愤填膺,有口者无不喟然长叹。然因奸臣位高权重,又蒙陛下信任嘉奖,众人惧得罪奸臣而断了自己退路,担忧事未举而灾祸已至,是以皆为自身计,而非为国家谋。
“臣近来还想着隐忍,不想揭发此事。其一,彼等罪恶昭彰,如山之积,人皆怨愤指责,声若雷霆。料想陛下圣明,一定会诛杀他们。其二,四方暂无战事,诸般政务已处理完毕,纵彼等暗中败坏纲常法纪,贿赂之风公然盛行,但等到他们恶贯满盈时,必定会自取灭亡。今逢凶徒祸乱,陛下忧心忡忡。但凡诏令之制定,皆关乎国家之安危。可恨此等奸贼竟肆意欺瞒君上,淆乱陛下之圣断,其恶行不止一端。陛下听了他们的话,又向近臣询问。他们相互勾结,一唱一和,蒙蔽迷惑陛下的视听。所以自臣讨贼以来,所陈之事都很紧要,而接到的诏书内容很多都与臣所奏不一致。可惜陛下对臣委以重任,而被奸臣所误也不少。
“臣素与诸奸佞之臣无冤无仇。日前,臣恳请乘驿车入朝,当面向陛下陈奏军情要事,此乃奸臣最为忌惮之举。彼等深知,若臣面圣,必能详述其过,因此千方百计阻止臣。臣又奏请统率各路兵马,协同并进,相机进击叛贼,却遭那伙奸臣党羽蓄意掣肘。他们生怕臣统领各道之军建功,因而致使臣进退维谷,所上奏章皆被拦截。他们还联合奸邪狡诈之徒对付臣,时而兵分两路前往招抚,却故意滞留长达十余日;时而派遣使者至蔚州行营,蓄意拖延时间。其用心不过是要令臣陷入困境,一事无成。至于天下之治乱、山东战事之胜负,他们全然抛诸脑后。身为臣子侍奉君主,竟恶劣至此。况且陛下身边忠良贤能之士众多,既有熟谙典章制度者,亦不乏精通军事之人,尽可任用。缘何独独重用此等奸佞之徒呢?依臣愚见,若能尽除朝中奸臣,那么河朔之乱,不待兴兵便会平定;倘若朝中奸臣仍在,即便平定了叛乱,亦难收长久之实效。
“臣研读本朝史籍,知悉代宗一朝,吐蕃等外族来犯,直逼都城。代宗却浑然不知,皆因被程元振蒙蔽,险些危及江山社稷。彼时,柳伉不过是太常寺一介博士,却能上奏章将罪责归于程元振,为国家除去大患。今臣位居要职,兼领将相之权,又怎能坐视奸佞之徒遮蔽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光辉?臣心中满是愤怒与痛恨!特将此奏疏交付宫廷使臣赵奉国呈予陛下。若陛下不信,依旧被奸臣蛊惑,恳请陛下将此篇奏表公之于众,令三事大夫与文武百官一同评议。若奸党未遭众人指斥,臣甘愿领受罪责。上天洞察一切,定能明鉴臣之忠心。只要天下人知晓臣不负陛下,即便到了身死之时,臣亦死而无憾,犹如重生。”
裴度接着又上了三道奏章,言辞恳切。穆宗见状,心中虽不悦,但忌惮大臣议论,于是改任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免去了元稹在宫廷内的要职。然而,穆宗对元稹的恩宠并未就此消减。没过多久,穆宗又授予元稹平章事之位,同时剥夺了裴度的兵权,改命他担任司徒、同平章事,并充任东都留守之职。谏官想劝穆宗收回此命,相继从便殿角门一路拜伏到延英门进谏。穆宗心里清楚他们所谏何事,却迟迟不肯及时召见。谏官无奈,皆上疏进言:“当下战事尚未平息,裴度兼具将相之才,不应将其安置于闲散无用之位。”穆宗深知人心所向皆为裴度,遂下诏令裴度由太原取道京师,前往洛阳赴任。元稹出任宰相之后,奏请皇上停止用兵,为王廷凑、朱克融洗刷罪名,解除深州之围。其真实意图是想要借此剥夺裴度的兵权。
长庆二年(822年)三月,裴度到达京城。面见穆宗之时,他先陈述朱克融、王廷凑在河朔地区发起暴乱,自己奉命讨贼无功,再陈述受职东都、准许他入朝觐见,感谢皇帝恩典。裴度在宫殿台阶前伏地启奏,泪水纵横。穆宗为之动容,道:“卿所奏谢恩之意朕已明晰。朕将于延英殿接见你。”众人皆以为裴度并无皇帝亲信之人助力,又遭奸佞小人排挤,纵然身负赫赫功名与威望,恐也难以打动皇帝。然而,裴度奏报河北讨贼之事时,慷慨激昂,声音震彻殿堂。文武百官无不为之动容,武将公卿亦有感慨落泪者。次日,穆宗任命裴度为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并晋升其为光禄大夫。
3修书破困 深州解围
彼时,朱克融、王廷凑虽已接受朝廷所授节钺,却并未解除对深州的围困。裴度刚从太原启程便分别致信二人,晓以大义。朱克融旋即解除围困撤离,王廷凑亦随之撤兵。有宫中使者奏报此事,穆宗闻之,龙颜大悦,当日即派遣使者前往深州迎接牛元翼返回,同时令裴度再次修书予王廷凑。
裴度自太原往京城途中接到诏书。使者接过裴度所写之信后建言:“大人朝见谢恩之后,即刻赴东都留守之任。只怕王廷凑得知大人已无兵权,会背弃先前约定。还望大人莫要再寄此信。”使者随即将裴度书信呈予皇帝,并详尽奏明此事缘由。待裴度抵达京城入朝奏对之时,穆宗正因深州之围忧心忡忡,于是当机立断,授予裴度淮南节度使一职。
4良策息争 智全君臣
在此之前,监军使刘承偕倚仗皇帝的恩宠,肆意欺凌节度使刘悟。三军将士群情激愤,将刘承偕拿下,欲将其诛杀。将士们斩杀了刘承偕的两名侍从。幸得刘悟出面,刘承偕才侥幸保住性命,不过仍被囚禁起来。穆宗颁下诏书,令刘承偕返回京城。刘悟却以军情为由,并未及时奉旨。
朝廷就此事展开讨论,宰相在延英殿奏对,裴度亦参与其中。穆宗看着裴度说:“刘悟拘禁刘承偕,拒不放他回朝,此事该如何处置?”裴度以藩臣不应议论军国大事为由婉言推辞。穆宗不依不饶,坚持追问:“刘悟辜负了朕的信任。朕以仆射之职厚待他,近日还赐给他五万匹绢。他不思立功以报皇恩,反倒纵容军队欺凌监军,实在令朕难以容忍。”
裴度回应道:“刘承偕在昭义地区肆意妄为、不守法度,这些情况臣都有所了解。前些日子,刘悟在行营给臣写信,详细列举了刘承偕的种种过错。当时,使者赵弘亮正在臣的军中,还取走了刘悟的信件,打算亲自上奏。不知他是否奏报了此事?”穆宗表示:“朕全然不知此事。刘悟为何不直接密奏于朕?难道朕还处置不了吗?”裴度说:“刘悟身为武将,不懂大臣奏事的规矩。虽说此事他做得不对,但臣私下认为,即便刘悟有密奏呈上,陛下恐怕也难以处置。如今事情已发展至此,臣等当面奏论,陛下尚且犹豫不决,仅凭刘悟的一面之词又怎能打动陛下呢?”
穆宗说:“过往之事暂且不提,直接说当下该如何处置吧。”裴度道:“陛下若真想收服忠臣义士之心,让天下武将为陛下尽忠效命、不惜死节,只需颁下诏书,承认自己用人失察致使刘承偕这般违法乱纪,命令刘悟当着三军将士的面斩杀他。如此一来,天下各方势力必定竭诚效命,叛贼也会闻风丧胆,天下便可太平无事。否则,臣担忧即便给刘悟改换官职、赏赐绢帛也无济于事。”
穆宗低头沉思许久后说:“朕并非舍不得刘承偕,只是他乃太后的义子,如今被囚禁,太后尚不知情。倘若你还未想好妥善的处置办法,可再商议合适之策。”裴度与王播等人又上奏:“只需将刘承偕流放到偏远之地,刘悟必定会放了他。”穆宗觉得此计可行。后来,刘承偕顺利返回京城。
5奸党构陷 孤臣去国
裴度初任司徒之际,徐州呈奏:“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部返还,驱逐了节度使崔群,自行宣称留后之职。”朝廷闻之上下震惊,当日便颁下诏书,命裴度依旧执掌朝政,同时委派宰相王播接替裴度镇守淮南。
裴度与李逢吉向来不和。裴度从太原入朝后,那些厌恶裴度之人觉得李逢吉擅使阴谋诡计,于是将他从襄阳召回朝中对付裴度。
裴度再度主政朝堂之后,魏弘简、刘承偕的党羽依旧盘踞宫中。李逢吉采用族子李仲言的计策,通过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勾连。宦官们皆愿意助力李逢吉。长庆二年(822年)五月,左神策军上奏称,告密者李赏声言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指使,勾结刺客企图刺杀裴度。穆宗颁下诏书,令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一同审讯于方一案。案件尚未审明,元稹便被免去同州刺史之职,裴度亦被免去左仆射之职,李逢吉则取代裴度成为宰相。
李逢吉的党羽李仲言、张又新、李续等人,内与宦官勾结,外则煽动官员,并结成朋党以阻挠裴度,当时号称“八关十六子”。裴度的“负面传闻”逐渐流传开来。不久,朝廷便将裴度外调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再兼任平章事。
6处厚力荐 贤相得用
长庆四年(824年),穆宗驾崩,敬宗李湛于穆宗灵柩前即位。同年,襄阳节度使牛元翼辞世。此前,牛元翼的家人一直身处镇州,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镇州接他们,王廷凑却百般拖延拒不放人。王廷凑听闻牛元翼已死,竟残忍地将其家人屠戮殆尽。敬宗得知此事后,一连数日叹息不已,感慨朝中宰相无能,致使奸臣如此嚣张跋扈、悖逆犯上。
翰林学士韦处厚进言:“臣听闻西汉之时,汲黯身处朝堂,淮南王便不敢图谋叛乱;战国之际,段干木居于魏国,诸侯便不敢贸然侵犯。一名有才之士足以抵挡百万雄师,一位贤能之人能够遏制千里灾祸。依臣之见,裴度功勋卓著,名震华夏,声扬外邦。王廷凑、朱克融之流惧怕他得到重用,吐蕃、回鹘亦钦佩他的威名。若能让裴度在朝廷任职,委以重任,那么西夷、北虏必定不敢觊觎中华大地,河北东部也必然会遵从朝廷诏令。况且幽州、镇州的叛乱尚未平定,此时尤其需要倚仗裴度这样的大臣。管仲曾言,‘偏听一人之言,会陷入愚昧无知;广泛听取众人意见,方能明智通达。’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并无其他诀窍,顺应民心便能治理得当,违背民心便会陷入混乱。臣听闻陛下连吃饭时都在叹息,遗憾朝中没有萧何、曹参那般的贤才,可如今裴度这样的人才就在眼前却不加以重用。这如同冯唐感慨汉文帝,若皇帝不够圣明,即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也无法任用。
“驾驭宰相之法,在于对其予以信任、亲近以及礼遇。倘若宰相处理政务毫无成效,于国家毫无功劳,那就将其安置于闲散职位,或是贬谪至偏远州郡。如此一来,在位官员必定勤勉努力,而谋求晋升之人也不敢随意钻营。陛下若能对宰相保持始终如一的恩遇,而非将其彻底弃用,那便是君臣之间至深的情谊了。如今,那些得到晋升的官员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被贬斥的官员却依旧能保住六部尚书这样的高位,不贤能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劝诫惩处。臣与李逢吉向来没有仇隙,也曾因某事被裴度贬官。如今臣所言,上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圣明,下是为了反映众人的议论。臣披肝沥胆,满怀感恩,伏地流泪进谏。恳请陛下明察臣的一片忠心,体谅臣为国家考虑的心意,这便是天下的万幸了。”
敬宗听闻此言,惊讶之余顿有所悟,看到裴度的奏状上没有平章事的头衔,便向韦处厚问道:“为何裴度的官职中没有平章事一职呢?”韦处厚上奏:“裴度被李逢吉排挤,离京镇守兴元,因而官职头衔中就被减去了平章事。”敬宗说:“何至于此呢。”次日便下达诏令,命裴度兼任同平章事之职。
7敬宗信任 裴度脱困
李逢吉的党羽耍尽手段诋毁、阻拦裴度,生怕裴度再得到重用。有个陈留人叫武昭,天性果敢且口才出众。裴度征讨淮西时,武昭主动请缨,投身军旅效力。裴度派他前往蔡州劝降吴元济。吴元济以武力相逼,试图恐吓武昭,可武昭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最终被以礼相待,平安归来。裴度觉得武昭是个人才,堪当重任,便在军中给他安排了职位。此后,武昭跟随裴度镇守太原。裴度还上奏朝廷,为武昭请封石州刺史一职。
武昭被免去石州刺史后,被授予袁王府长史的职位。武昭身处闲职,心里有些郁闷,并且有抱怨李逢吉的言论。那些奸党见有机可乘,便指使卫尉卿刘遵古的随从安再荣出面告发,声称武昭图谋不轨,欲谋害李逢吉。这案子草草审结,武昭含冤被处死。奸党妄图借此机会牵连裴度。然而,朝中士大夫秉持公正,纷纷站在裴度这边,指责李逢吉的所作所为。敬宗也逐渐了解事情的真相。此后,但凡宫中使者途经兴元,必定会传达秘密旨意,对裴度加以抚慰,还隐约透露出将征召他回朝的意向。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十一月,裴度呈上奏疏,恳请入朝觐见皇帝。次年正月,裴度抵达京城。敬宗对他礼遇有加,没过几日便颁下诏书,再度命裴度执掌朝政。李逢吉党羽中的左拾遗张权舆不遗余力地诋毁裴度。在裴度从兴元请求入朝之际,张权舆赶忙上疏:“裴度之名,与图谶暗合,其宅邸又占据山冈高处。如今不召自来,他的心思不言而喻。”在此之前,李逢吉那一伙奸佞之徒忌恨裴度,特意编造了一首童谣:“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其中“天”“口” 二字暗指裴度派人劝降吴元济之事。京城东西走向横卧着六道山冈,恰似乾卦之象。裴度位于平乐里的府邸恰巧坐落在第五道山冈之上。于是,张权舆便拿这些大做文章,编排裴度,妄图以此诬陷裴度有“不轨之心”。
敬宗年纪尚轻,却头脑清醒,深知这是对裴度的恶意诽谤,对裴度的赞赏与信任丝毫不减。那些奸邪小人再难兴风作浪了。
8谏止东巡 靖邦安民
宝历二年(826年),敬宗计划巡幸东都洛阳。宰相李逢吉以及门下、中书两省的谏官多次呈上奏疏,极力劝阻。敬宗一脸严肃,语气坚决地说:“朕东巡的心意已决。随行的官员和宫人皆自行准备干粮,绝不会劳烦百姓供给。”李逢吉赶忙跪地进谏:“东都洛阳距此千里之遥。按例巡幸本属常事,但陛下一旦出行,万事皆须依照礼仪,千乘万骑相随,规模难以缩减。即便不必极尽奢华,也需做到丰俭适宜,怎能让随行之人自备干粮?这岂不是有失皇家体统?当下战事尚未全然平息,边境地区也未彻底安宁。如此行事恐怕会引发人心动荡。恳请陛下稍作思量,回心转意。”然而,敬宗并未听从,随即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赶赴东都,检查沿途行营以及洛阳皇宫状况。
朝廷大臣正忧虑惶恐,恰逢裴度从兴元入朝。在延英殿奏事之际,因敬宗谈及巡幸一事,裴度说:“国家营建东西二都,本意就是为了方便帝王巡幸。自从国家历经艰难变故,这一做法便搁置了。东都洛阳的宫殿,连同六军的营垒、各部门的官署大多已荒废。陛下若执意前往巡幸,必定要稍加修缮整理。如此一来,至少得花费一年半载筹备之后方可再议出行之事。”敬宗听后道:“群臣进谏时,并未考虑到这些情况,只是一味劝阻朕不该前往。若真如你所言,那不去也罢,或者将巡幸日期往后推迟。”不久后,朱克融、史宪诚各自上书,请求派遣五千工匠协助修缮东都洛阳。敬宗见此便搁置了东巡计划。
9辅君献谋 解纷纾困
幽州的朱克融将赏赐春衣的使者杨文端扣留,上奏称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还上奏说今年三军的春衣数量不足,请求度支府拨发一个季度的春衣约三十万端匹,并派遣五千工匠协助修复东都洛阳。敬宗听闻,忧虑朱克融的态度不恭,便询问宰相:“朱克融所奏之事,应当如何处置?朕想派一位重臣前去宣谕抚慰,顺便将被扣留的春衣使者接回。这样做可行吗?”
裴度回应道:“朱克融一族本就凶狠残暴,如今无端做出这般傲慢悖逆之事,注定会自食恶果。陛下不必为此忧虑。这就好比豺狼虎豹在山林之中肆意吼叫跳跃,可若对其不理不睬,它也无计可施。这个逆贼只敢在自己的巢穴里放肆无礼,一旦离开巢穴外出行动便没了底气。当下,既无需派遣使者前往宣谕抚慰,也不必急着接回被扣留的使者。再等十来天,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听闻朝廷使臣在你处有不当举止,待其归来,朕自会处置。赏赐于你的春衣,相关部门制作时不够用心,朕定会彻查此事,现已下令着手处理。’至于他请求派遣五千工匠以及军队前往东都洛阳一事,分明是虚情假意。臣料想逆贼根本无法派出人手。如今若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计,便回复他:‘你所请求派遣工匠修缮宫殿一事,可尽快派人前来。朕已下令魏州、博州等道在当地妥善安排接应。’料想朱克融收到这道诏书,必定会惊慌失措。倘若陛下不想如此强硬,仍想表示宽容,那就回复他:‘东都洛阳需修缮之处,自有相关部门负责,无需你派遣工匠长途跋涉而来。你提及的三军春衣,本就是各道自行操办的日常事务。近来朝廷偶有赏赐,皆是因征调当地人力物资才给予优厚恩赏,平常并无此惯例。朕并非吝惜那二三十万端匹春衣,只是按规矩不能对范阳特殊对待,望你能明白。’如此处理即可,陛下切莫再为此事烦忧。”
敬宗采纳了裴度的建议,并让他进呈诏书拟文。果不其然,事情的发展如裴度所预料,不到十天,幽州内部便发生变故,朱克融及其两个儿子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