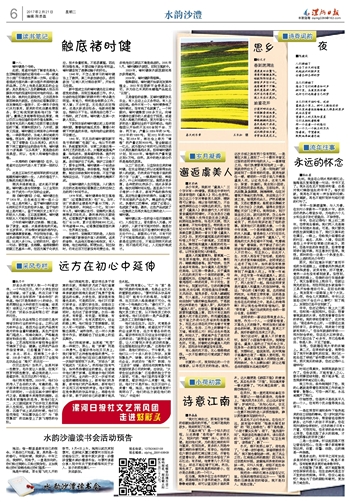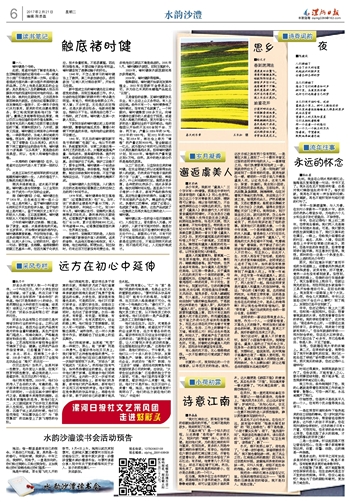■李晶晶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江南不是我的故乡,我却来到了江南。
“孔雀东南飞”是一个恒久的过程,从还操着“洛阳音”的东晋大夫, 到宋代的“南渡”诗人,前仆后继。起初他们来,为的是江南的和平与富庶,但到后来,更多的人则是冲着江南的诗意而来。有李白,他徘徊在六朝古迹的江南丘陵之间,尽管也还望着长安,最终却把生命留在了采石江边;有苏轼,他常常几个月不在任上,却总不能忘情于江南。然后,我也来了,虽然我是那样的渺小,但亦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行人。
在乌镇,我停步在立志书院的门前,那是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柴扉静静地锁着,却可以望见院子里的草木,这大概便是《游园不值》的意境吧。其实也并非“不值”,到乌镇来看一看水就够了。“河水清且涟漪”,涟漪仿佛诗行。
在苏州,我一直把笔和纸拿在手里,我要记——随处都是诗,沧浪亭上,“清风明月本无价,近山远水皆有情”;护城河边,“共知心似水,安见我非鱼”。最有意思的是在拙政园,听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讲那些楹联,辨认那些篆体写就的句子。
其实也不必行色匆匆。在住处不远,就有闺中裙钗“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陌上杨柳色”;柳下是池塘,“小荷才露尖尖角”;荷下,“鱼戏莲叶间”。我就坐在池塘边读书,读白居易的“江南好”,读王维的“红豆生南国”,读得痴了、醉了……
冬天,柳不再那么绿了,荷也残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不禁也像陆游一样,起了风尘之叹:江南是这样的脆弱!因为她太过阴柔和纤弱,就像她所养育的林妹妹一样,只叫人怜爱,却经不起生命的考验。多少楼台,都付烟雨中!
我把诗一样的江南永远留在记忆里,但我的理想却在远方——“我得得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