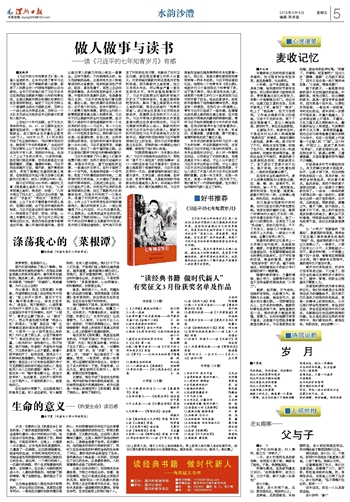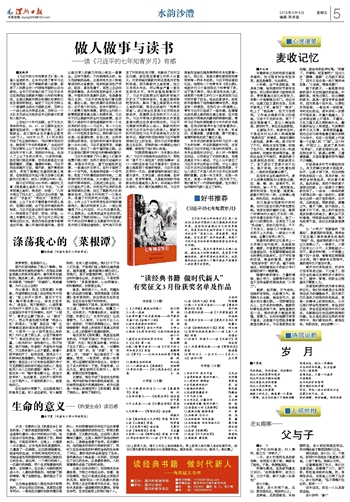■孙永辉
辛勤耕耘之后的收获无疑是幸福的,但过程有时会有些辛苦,甚至是痛苦,比如麦收。
小时候,由于体质较差,我身单力薄,每到麦收时节都有些害怕,所以那时候学习就特别用功,梦想着通过自己刻苦努力,有朝一日能够跳出农门,走出农村,远离又脏又累的农活。后来尽管考上了学,拿到了“粮本”,吃上了“商品粮”,但万万没想到,工作地点离家仅有三四里地,父母干不完的农活,我下了班还得接着干,更让人懊恼的是,麦收时节,单位还会放麦假。
五黄陆月天,焦麦炸豆时。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人很难理解“焦麦炸豆”的意思,稍谙农事的人都知道,麦熟一晌。麦子收早了不行,籽粒还没有顶满,收晚了也不行,熟透的麦子风一吹就会掉籽,收割时更掉得厉害。麦收还会受天气制约,熟透的麦子如果遇到连阴雨,那就麻烦大了,变了质出了芽麦子卖不出去,换不来钱,自己吃着也粘牙,一季的辛苦就算白费了。
在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麦子从成熟到颗粒归仓要经过割、拉、摊、碾、扬、装等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周而复始。麦收时间紧、任务重、强度高,就像行军打仗一样,必须精心准备,待机而动,决战决胜。
自己能参与到麦收中的时候,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饱受饥饿折磨的父母,像那个时候神州大地亿万农民一样,似乎有着无穷的干劲儿,除了一家六口的责任田,还承包了几亩“机动地”。奶奶已经年迈,干不了农活儿,姊妹几个年龄尚小,还排不上大用场,一家老小十来亩地,全靠父母劳心劳力。
我最早的麦收记忆是早上一大早被父母叫起来,去地里拾麦、耧麦,尽管麦茬会把脚脖划出道道血印,也屁颠屁颠地在狭长的责任田里奔忙。出于对饥饿的恐惧、粮食的敬畏,更源于“粒粒皆辛苦”的不易,毫不夸张地说,刚刚填饱肚子的老少爷们都唯恐掉下一颗麦穗。
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的增强,缺少劳力、急需帮手的父母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培养成“小劳力”。
割麦,起早割,天气凉快,但秸秆有韧性,比较费力气;等到晌午头去割,能省些气力,就是太阳太毒太晒。一顶草帽顶在头上,出汗多的时候热,割麦的时候也容易掉下来,索性直接扔在一边。倒伏的麦子割起来更慢,更费力。长时间弯腰弓背苦不堪言,总是禁不住想起身看看麦垄还剩多长,可总是姿势还没站稳,就会传来连声吆喝:“别看了,早着呢,赶紧割吧!”说过几次“腰痛、歇歇”之后就不再说了,因为父母总是一脸不屑的神回复:“小孩家,哪里有腰!”
割下的麦子,一般是要用自家的架子车拉到造好的场里。汗颜的是,我曳过稍儿、拉过满载的麦车,就是一直没有学会装麦车,因为那是个技术活。从责任田到场里,一般会有一段距离,有时还比较远,麦车讲究一次要尽可能多装,尽量少跑趟儿,又必须保证路上不塌车、不翻车,又饥又渴又热又晒的晌午头,翻车真的会让人很绝望。可成熟的麦秆又光又滑,装得层层叠叠、前后左右匀称考验着庄稼汉的眼力与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庄稼人的“门面”。这个时候,阡陌之上,就成了麦车的“走秀场”,大家在暗自比拼,也在相互学习,既真心称赞,又善意提醒,为紧张繁重的劳作增添不少情趣。
打场是诸多环节中最脏的活儿。用叉把碾过的麦子挑起来,抖开,让麦子掉下来,而后把秸秆挑走垛在一边,再用木锨、扫帚把余籽堆起来,然后看天等风,趁风扬场,再把干净的麦子装袋运回家,这一场麦子才算收获完毕了。一亩亩、一垛垛的麦子都得这样一场一场的打,都要经过这样一成不变的程序。这中间,这家起场,那家扬场,麦糠土气,漫天飞舞,防不胜防。几场麦子打下来,脸上的汗斑往往是皮肤最白的地方,鼻孔如不及时清理,呼吸都会成问题,嗓子也经常干涩,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从“小劳力”到家里的“顶梁柱”,最直观的体现是,我学会了在庄稼人看来难度也极高的“扬场”活。装成袋的麦子也不再让父亲操心了。一袋麦子,小袋少说有七八十斤,大袋能超过一百斤。最多的时候,一天我搬上搬下四十多袋,看看现在稍微提点东西,爬个楼都有点想喘气,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好多年已没有再进过场、下过地了,因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真的太快了,播种、管理、收获全过程基本不需要人力。
当曾经的麦收成为渐去渐远的记忆,我们终将感恩过去艰苦劳动岁月的慷慨给予,因为那不仅仅是体力极限的终极挑战,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洗礼,从中让我们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友好互助,学会在坚韧坚持中积少成多,化解貌似无法完成的困难和问题。也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辛苦劳作中,我们感知自然,感悟生命,收获自信,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