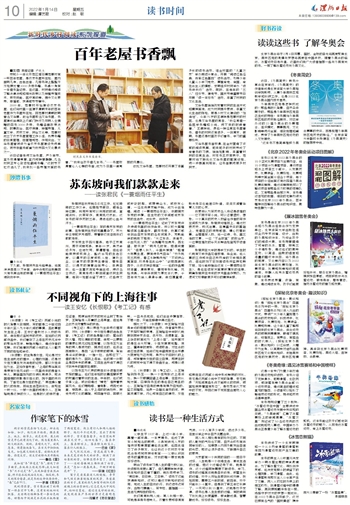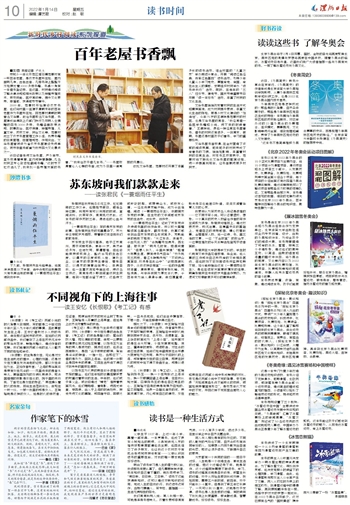■穆 丹
《长恨歌》与《考工记》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间的事情,且故事都发生在上海。王安忆借助对小人物的书写,连缀起这座城市的历史。在她的这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上海在历史沉浮中的繁华与苍凉、鲜艳与黯淡。通过作者的笔触,我们能看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长恨歌》的主角是女性。无论是对女性生活轨迹的描绘、心理的刻画,还是对女性友情生发与消逝的记录,都以女性体验为主。正如作者所言:“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带有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香水味儿,橱窗里陈列的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的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男性操纵着时代的走向,而将生活落到实处,体现在一针一线、一粥一饭里的却是女人。王琦瑶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是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即便后来历史的变迁尘封了繁华梦,王琦瑶走入平庸的上海弄堂,但她身上依然流动着繁华的底色。
《考工记》是以男性为主体进行描写的。对比《长恨歌》中女性场景的活色生香,《考工记》的底色是暗淡的:雪白的防火墙、斑驳凋敝的老屋,连那一丝朦胧的情愫也被沉闷地压制着。以陈书玉为主角的男人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他去往西南联大,是因“奚子殷殷的眼神,背后是采采的暖香,一推一拉,当即应下”。借的是外力。回到上海后,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因朱朱的邀请,又因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到朱朱的画报社谋职。
以陈书玉为代表的男性似乎很难突破家庭的壁垒。他们在年轻时依靠祖辈积累的财富过着殷实的生活。中年时,他们或子承父业,或依旧通过“啃老”维持着表面风光。他们喝咖啡、看电影、进西式学堂、穿西装,出入于上海的时尚场所,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却因循守旧、困顿乏味。一旦失去庇佑,他们往往步履维艰、不堪一击,只能在躲避中得过且过。
相比之下,《长恨歌》中王琦瑶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则更为主动。作者首先弱化了家庭环境的束缚,王琦瑶在中学时代就搬到同学家去住,去片场、去摄影室,登上杂志封面成为“上海小姐”。她所面对的是社会大环境,个性发展更完整、独立,懂得审时度势、进退取舍,对社会的适应性很强。她迫切地希望拥抱社会并最大限度地为己所用。虽然处于旧时代的上海,却有着新女性的自立自强。即便在时代的转变中她不得不委曲求全,却是以退为进。
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王琦瑶到陈书玉——换一个性别抵达上海深处,换一双眼睛回望上海往事。在自我认知方面,囚禁陈书玉的是他自己苟且的心。王琦瑶对自身的美是有强烈自知的,坚忍而璀璨。她像一条暗流涌动的河,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有自己的律动。女性和男性在这两部小说中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宅是这两部小说中不变的背景。老宅就像“天地间某些永远不能转化的物质,顽固地保持着固有形态”,是动荡年代万变中的不变,并因这种不变而显出撼动人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