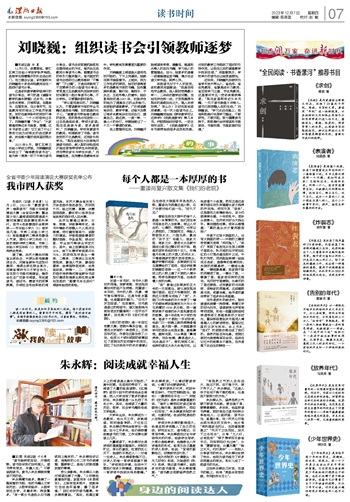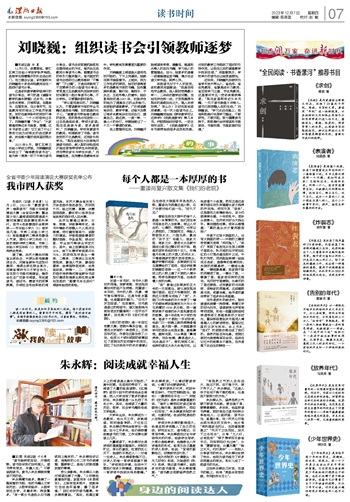■安小悠
初读一本书时,与书中人物初次相逢,有新奇感、有欲知后事如何的迫不及待感。而重读一本书时,书中的人物、风景、情节皆似曾相识。这是与故友重逢,也是重读的魅力。“旧书不厌百回读。”在我看来,旧书就是读过的那些书。谁又能拒绝与故知老友的重逢呢?一百次也不嫌多,如肖复兴的《我们的老院》。
《我们的老院》是一本回忆性散文集。老院叫粤东会馆,坐落在北京城的一条老街上,已有百年历史。作者在这里生活了21年。他用35个或长或短的故事回忆了老院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回忆了似水流年中的点点滴滴以及生活在大院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重读此书再遇这些人物,忍不住要对他们说一句,“好久不见!”
曾经生活在大院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他们用生命书写各自的人生故事,有让人怀念的、心痛的、惋惜的,也有让人愤恨的。刀郎腿阿玉、神秘人物欧阳太太、六指兄弟、最后的“孩子王”毛蛋儿、连家大姐、商家三女、姜老太太及新中国成立前当过舞女的毛子妈、跑堂的老宋和他的两个女儿、长得像月份牌上的大美人的何太太、只喝盖碗茶的美术老师老袁头、戴罗宋帽的老梁、东跨院的玉石及提携他的丁老师、很会讲故事的裱糊匠老吴……这一个个跃然纸上的人物上演了大院的人情冷暖,即使在黑暗岁月里,也涌动着人性的光辉。
“我”曾偷过东厢房的王大爷的一只泥斑马,被父亲发现后强行退回。但王大爷搬走时,竟把这只泥斑马送给了“我”。大院门口炸油条的牛大爷穿了一辈子的破油棉袄里竟有为大牛小牛兄弟藏的1000多元钱。因一套煎饼果子结缘的孙大姐和秦老师的故事,是十年动乱中少有的传奇。杨家个个都拉一手好京胡,他家门口一到晚上就热闹得像唱堂会,是大院一景。大院里最有学问的老孙头终身未娶,爱闻鼻烟,爱种花草,口头禅是“鼻烟养神,花朵怡情;鼻烟是女人,花朵是孩子”。闹饥荒那几年,他种的倭瓜大朵大朵地开花,让他家像个小金屋。然而正是这金黄的倭瓜花引来隔壁白家大妈养的芦花鸡,进而引发“恶战”。这场唇舌之战精彩绝伦,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十年动乱中,老孙头被揪斗,生死攸关时白大妈出手。事后提起往事,老孙头感慨道:“真的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呀!”
作者不仅写大院里的人,也写大院里的树——中院的三棵老枣树夏天老闹“吊死鬼儿”,“我们”常捉了偷放在女生身上或脖子里取乐。秋天结的马牙枣如红红的小灯笼点缀在枝叶之间,中秋打完枣,用洗脸盆装满一盆盆送去各家,是难得的温情时刻。后院的两棵桑树,一棵结白桑葚,一棵结紫桑葚。我家院子里的两棵老丁香,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杨家老四种的迟桂花,花开时节香满院,比春天的丁香还要香。还有景家的无花果树、老钟家的爬墙虎,这些植物虽无言,却最治愈,给作者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温暖。
在作者质朴的叙述中,始终缓缓流淌着一种深情。乘着文字的时光列车,读者被悄无声息地带进老院,和他一起重回那些纯净透明却又易碰易碎的少年时光,重识那些斑驳岁月里用人情温暖人心的新老街坊,重温记忆里的北京与流年。合上书本,“我们”的老院仿佛也成了我们的。虽然历经百年沧桑,老院已被时光剥落得面目全非,但刻在记忆中的故事永不褪色,在作者笔下永远生动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