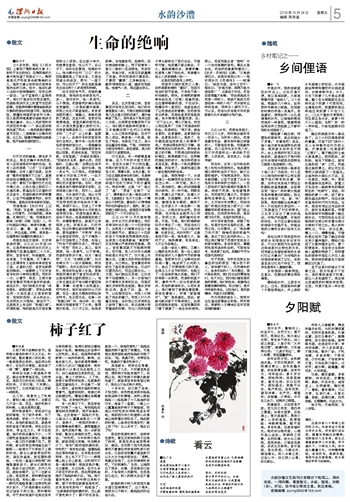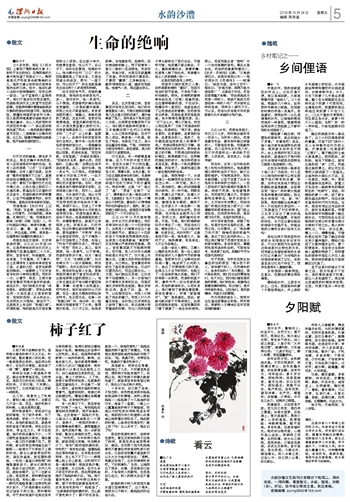■张乃千
三十多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陶斯亮的文章中我知道了范滂这个人。陶斯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女儿,她的文章以信的形式哀悼含冤死去的父亲。信中,她回忆家人去狱中探视陶铸时,写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读这段话使我知道了两点:一是范滂是汉朝的直节忠臣;二是陶铸十分敬仰范滂。这之后,随着对陶铸的由衷崇敬,我开始被范滂所吸引。
一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在史籍中寻找范滂。有人说范滂是范仲淹的先祖;也有人说范滂是“三苏”父子崇拜的偶像;还有人援引经典,说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直接效法他去慷慨赴死。而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沙澧河交汇处在许慎之后、公孙大娘之前的又一汉唐风骨。那遥远而又沉重的历史足音中,范滂的脚步声异常震耳,以至于响越魏晋两宋,咏叹于明清,直抵后世革命家的耳鼓。
范滂是谁?《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哦,范滂是东汉郾城(汝南)召陵(征羌)人,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官后公、廉、勤、谨(光禄四行),声名远播。好啊,原来是一位值得我们夸耀的先辈老乡!
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是两帝统治的东汉历史上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那时,宦官专权,时政腐败,贤良受害,万民罹难,天下豪杰、名士及儒学有义者纷纷举劾宦官之恶,正直的大臣、官员也都群起而弹劾。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相当激烈。而权奸一方,以曹节、侯览、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凭借对皇权的渗透,疯狂反扑,他们诬称反对者“结党营私、欲图社稷”,罗织各种罪名把一大批忠直之士罢官的罢官、投狱的投狱、杀头的杀头,先后两次大兴冤狱,振动天下,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所谓党锢,指的就是反对宦官集团的士人贤吏。在这场斗争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心。他与朝中位列“三公”的大臣陈蕃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那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名言就是最先出自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呐喊。
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然刚直,使他的生命骄若松竹。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从不畏惧。范滂曾两次牵头惩治官吏腐败,一次是赴冀州案察,所到之处无不深查细究。有官吏妄图利惠之、情融之,都被范滂抓了典型。及至州府,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皆望风解印绶而去。另一次是负责监督大吏的行为,范滂直指黑恶势力,一连弹劾刺史和“二千石”以上权豪、显要二十余人。此举对专权的宦官体系打击很大。朝中有一位尚书责怪范滂弹劾面过大,一是提醒他小心为妙,二是怀疑他是否挟私怨以报复。范滂坦言道:“若臣有贰,甘受显戮。”并阐述其理说:“臣闻农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说得这位尚书连连称是。其二,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范滂辅助汝南太守宗慈工作时,一丝不苟,凡有违孝悌、失仁义者,一律处罚并直接开除。当时,范滂恰遇其亲外甥李颂谋求官职,这李颂是公族子孙,西平人,品质顽劣,为乡里所不齿。他以为凭着舅父的权力就可以谋取官位,可没想到范滂对他始终不屑一顾。李颂不甘心,巴结上了中常侍唐衡,唐衡就指令太守宗慈允诺李颂为官。范滂知道此事后,坚决不答应。他虽是辅助宗慈工作,却掌管着吏位,就是不让李颂来上任。宗慈无奈,只好作罢。但这件事也就间接得罪了唐衡,要知道朝中“中常侍”的位子全被宦官把持,这下子阉党一脉不仅加倍恨上了范滂,也恼上了听命于范滂的许多人,呼他们为“范党”而仇之。其三,面对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范滂的官职并不高,初为“清诏使”,又为“光禄勋主事”,后为汝南太守(一说只是辅助,相当于副职)。也许正因为处于中层官阶,使他有机会深入乡里,更能洞悉民情并敢于直言民间疾苦,这是他深得众望的原因之一。他之有名望还在于他与朝中重臣陈蕃、李膺、杜密等人志同道合,同气相求,面对汹汹权奸从不折腰,而且一直在为颓废的纲纪奔走呼号。也正因为此,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与李、杜一起被视为党锢首领下了大牢。值得莞尔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侥幸获释,当他离洛阳,经南阳,回汝南老家的路上,想不到竟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在迎颂他,有老百姓,有地方官,光是马车就塞满了官道。然而范滂却不愿扰民,不愿因“戴罪”之身牵连他人,毅然悄悄改走小道,幽夜回到故里。他清气一身,视名望如浮云。
二
其实,这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本意是要杀人的。可是汉桓帝在陈蕃等几位正直大臣的劝谏下,意外地释放了党人,条件是永不再用这些人为官。这使得宦官集团很不甘心,他们既未能除掉范滂等人,又未能撼动那个位列三公的陈蕃,心头之恨依然鼓鼓。但对于党人来说,释放是一个机遇,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实力,其斗志丝毫没有消减。于是,对峙的双方都没有停手,都在密谋,更大的风雨不久就要到来。
行文至此,有一种感慨直逼笔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宫廷史占据了不少的位置。而我们的宫廷史,其实就是一部宫斗史,黑幕太深,玄机太重。权力在这里既是争夺的目标,也是争夺的手段,宫墙高耸,宫帷低垂,却遮不住权力异化下的尔虞我诈。很多时候,这里“术”胜过了“道”,“邪恶”压制了“正义”,儒学教化只是一堆苍白的文字,《道德经》也只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的呓语,善良的人们常常被作奸犯科者钻空子。是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就是因为宦官集团抓住了一个天大的空子。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驾崩,次年正月汉灵帝继位。而汉灵帝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如果党人们能够关注这个皇权交接的节点,重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可能被思想绑架的风险;如果党人也能果断地“清君侧”并及时施以严密的防范措施,那么,宦官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得手。但可惜,党人们兴许太麻痹抑或是太书生气了,仅只是上书窦太后,让窦太后协同幼帝惩治宦官。与之相比,宦官集团牢牢抓住了皇权更迭的机会,行动不仅雷厉风行,而且凶狠无比。一方面,他们游说汉灵帝,让汉灵帝下诏逮捕党人;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傻等汉灵帝的反应,而是买通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毒杀灵帝的近侍,盗走了印、玺、符、节,以此假传诏令,向党人们举起了拘杀的屠刀。而党人们几乎毫无防备,当奸党以汉灵帝的名义劫持了窦太后,派兵追捕大将军窦武的时候,年过八旬的陈蕃才率太尉府兵丁进行还击,可惜呀可惜,他因寡不敌众被杀,不久,窦武被擒自杀,接着李膺、杜密等人被下狱处死,再接着大批士人贤吏被捕入狱……
还是回到范滂身上来吧。
范滂早已被奸党恨之入骨,自然是要抓捕的“重犯”,但因为他当时居于故里,才幸免于第一时间被抓。很快,汝南郡的督邮奉命赴征羌(召陵)捉拿范滂。这位督邮敬佩范滂,不忍动手,抱着诏书一直哭泣,他甚至表达了让范滂逃走的意愿。但范滂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来到县里投案。县令郭揖也敬重范滂,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你怎么到这里来?”又给了范滂逃命的机会。范滂却说:“我不来,就会连累你,连累督邮,连累我的母亲,连累更多的人。我来了,也许朝廷就会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范滂说得坦然而又平静,是那种视死如归的坦然,那种舍身就义的平静,引得周边的狱吏纷纷啜泣。郭揖感佩万分,在押解范滂赴京的前夕,他安排范滂与其母见面。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薄暮,范母来了,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的会面。
这里,我想停顿一下,与读者诸公一起猜想范母见到儿子时会怎么样:一种可能,执儿之手,涕泪滂沱,痛心的话语随着泪水倾泻;另一种可能,两眼呆滞,伤痛几近于麻木,扯着儿子的衣襟,无语凝咽;还有一种可能,跪倒在县令跟前,痛哭不已,泣求放儿子一条生路……慈母之心,大抵应该如此吧。若讲特殊,也许她还会绝然与儿同在,哭别之后,旋即撞死在牢前。可是,可是,我们的揣测都似乎太常态了一些,范母泪光闪烁,竟语出惊人:“儿近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真是惊天的一语,她告慰儿子,能死于义,她很满意,有其弟在,儿不必为母难过。
这是一场出人意料,又撼人心魄的生死决别,是一位心境芬芳的母亲对儿子凛然气节的深情嘉勉,是哲学日历上诠释死生的惊鸿一瞥。她送别了必死的儿子,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不屈,在捍卫儿子名节的同时,也挺立了一位母亲的高大形象。我们不妨再做一点联想,范滂的刚直不阿,凛然气节一定与范家的家风、范母的教诲有关。从范氏身上,我们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做官连着做人,所谓“家国情怀”,“家”是根基也。因此,家教与家风皆不可等闲视之。如果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团的刀锋下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三
公元169年,范滂舍身就义,年仅三十三岁,同时被杀害的有一百多人。与所有人相比,范滂是最有机会、最有条件躲过祸害的人,可是他没有躲,而是毅然就害。后人在评论东汉党人时,无不对范滂的这一举动给予泣赞:儿伏其死,母欢其义,壮哉伟哉!
而当时,还有一位叫张俭的党人恰恰与范滂相反。他逃避党锢之祸的机会并不充分,缺少必要的掩护。可他顾其身阶,到处东躲西藏,以至于连累了众多与他有关系和保护过他的人,一些人因他的不能归案被奸党屠身灭族。相较于范滂,张俭羞愧弗如,而范滂则义薄云天。范滂的影响足够深远,除苏东坡母子外,文天祥亦有诗赞之,而流传甚广的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那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没有提范滂,却提了张俭,恰是对生死去留的反思,褒抑之间,壮怀激烈,以“我自横刀向天笑”隐喻范滂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自己赴死的决心。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范滂对变法志士的深刻影响。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也是有逃命机会的,可是他没有,他选择了赴死。其胸怀气节与范滂何其相似!
对于范滂,当然也包括正如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和无数近、现代革命英烈,我们无论如何赞美他们,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曾经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生命,都轰鸣过振聋发聩的绝响。有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记住他们,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需要。
作为范滂的故乡人,我想对这位遥远前辈表达的是:两河岸边,崭新的人文精神正在书写更宏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