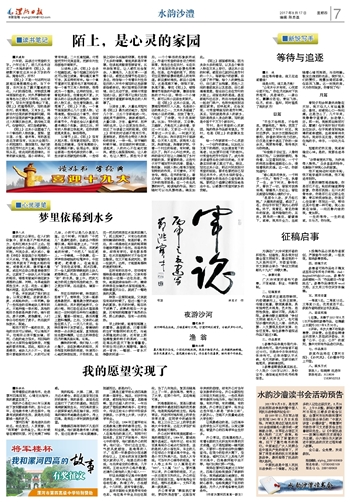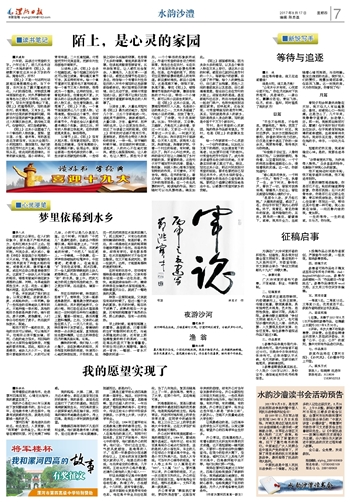■李人庆
老家在大山深处,在人们的印象中,原本是不产稻米的地方,也和江南水乡沾不上边。但老家地处伏牛山腹地,四周群山环抱,河流众多,或大或小,像是《诗经》里窈窕少女甩落的一只只水袖。于是,勤劳智慧的先辈们很早就有了种植水稻的传统,或修筑水库、塘坝蓄水灌溉,或在河边依山势直接修渠引水,这就有了一块块儿水平如镜的稻田,错落有致地环绕在家乡周围的山脚、河畔,与旱地里的那些玉米、大豆、花生、红薯们隔水相望,在风中轻声呢喃。
于是,米饭就成了我们的主食。从我记事起,老家都是小麦、水稻轮种的,一年两熟。除了一些低洼的沼泽地块儿常年积水,只能种植一季水稻,其他的稻田冬季都是种麦子的。端午前后,麦子成熟,麦浪翻滚,人们争分夺秒抢收了麦子,然后就开始放水、犁地。
稻田不同于一般的农田,其他的农田可以倾斜,可以高低不平。但稻田必须平整如镜,否则,凸起的地方没水,而凹陷的地方水太深则会淹没秧苗,对整地的要求很高。因此,稻田大多是梯田,地块儿大小不一,依地势只要能保持水平,大的可以有几亩,小的可以是几分甚至几厘。这个时候,村里的“牛把儿”是最吃香的,各家各户得排着队请。稻田里放上水,“牛把儿”先用犁铧犁,然后,用耙耙地的时候,“牛把儿”站在耙上,一手牵绳,一手执鞭,在一声声抑扬顿挫的吆喝声中,牛拉着耙,耙载着人,在地里呈“8”字形往返穿插,泥水四溅,不一会儿就把犁铧掀起的土块儿耙得稀烂。然后,还要用一种叫“耖”的农具,套上牛,把突兀地方的泥土推向低洼的地方,使之更加平展,远远望去,镜面一般。
早在谷雨的时候,秧苗就已经育下了。育秧苗,父亲一般都选择最肥沃、灌溉最方便的地块儿做秧田,用木筢把地弄平,分成小畦,将已经在适当水温里浸泡过一定时间的谷种均匀地撒在上面,覆盖一层细土,最后再覆上塑料薄膜。之后,父亲的心就拴在那儿了,一天几个来回,去秧田看种子发芽破土,看嫩绿的秧苗一点点拱出地面,直到轻轻扯去塑料薄膜,让出土的秧苗在四月的熏风里长高,长高。
薅秧的时候,我们每人一把小凳子,坐在放满水的稻田,用手指紧扣秧苗的根部,快速而小心地把秧苗扯脱,不伤根须。扯完一把后把根须在水里来回涮几下,泥土脱掉了,只有白色的根须和嫩绿的秧苗,煞是好看。然后,用一根浸泡在水里的稻草顺手缠绕两圈系个活扣。活虽然简单,却很有学问,首先要系得紧,往水田里抛秧时才不会在半空散架。但又不能系成死扣,要一扯就开,这样,才能提高插秧的速度和效率。
在所有的农活中,恐怕唯有插秧是倒退着进行的,父亲和哥哥姐姐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很快,地里就绿油油的一片,嫩绿的秧苗在如镜的水面轻轻摇曳,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
秧苗一旦插到地里,父亲就没有闲的时候了。经过一整个炎热的夏季,秋天的时候,稻谷终于成熟了。成熟的稻谷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垂下高昂的头颅,那么的谦恭,没有一点的张扬。
早上的时候,能看到稻穗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闪着田野的空旷和黎明时的光芒,与地头那隆起的山坡,还有坡上那挂满橙黄的柿子的果树,一起在高远的蓝天下散发着馨香,听排空而过的大雁歌唱,融化成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永不停歇的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