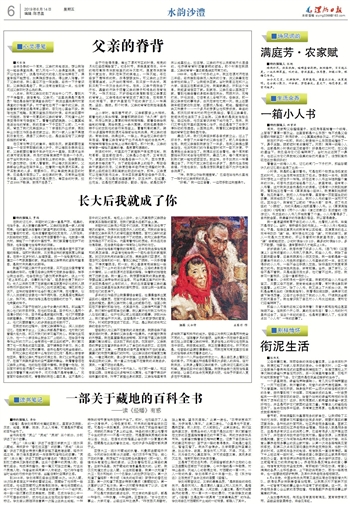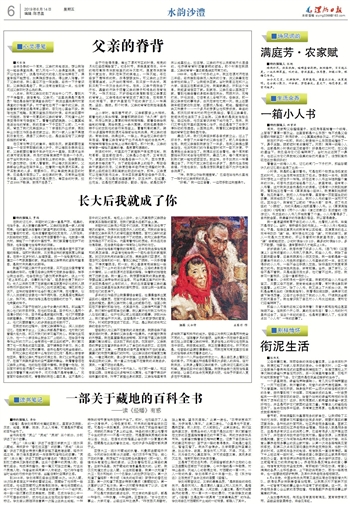■特约撰稿人 李玲
《经幡》是徐剑将军的长篇纪实散文,里面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军事、旅游、风土人情等,可谓是关于藏地的百科全书了。
全书共包括“灵山”“灵地”“灵湖”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三个故事。
“灵山”(共12篇)讲述了法国汉学家大卫·妮尔深入藏地、寻找梦中“香巴拉王国”的故事;“灵地”(共22篇)讲述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穿越万里羌塘进藏,昭示怀远之情、努力维系国家统一与族群和谐相处的故事;“灵湖”(共21篇)讲述了西藏当时著名的“摄政王热振”达到权力巅峰又跌落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灵魂人物,经有机组合,构成浑然整体,每一篇又可独立成篇。对这三个灵魂人物,作者全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与作者在当时当地的行旅中进行对话,丝毫没有时空隔断之感。
到2018年,徐剑将军已经去过西藏18次。18次入藏,18次贴身感受这片神奇的雪域之地,西藏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观感。他也因西藏而让灵魂得到淬华。等他将西藏的土地一寸寸地走完,将五千年蕴含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听完,将一段一段沉厚的历史串接完,西藏,已成为徐剑心中一个不可磨去的烙印,成为他此生此世无比珍惜的一个地域标记。徐剑自从跟随阴法唐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起,一种特殊的情节便悄然在胸中产生了。那时,他刚经历了人生的一次滑铁卢,心情极度低郁,对未来的路有些拔剑四顾。可是他一来到高原,炽热的阳光烤炙了那些疼痛的回忆,清朗的风拂去了身上的尘埃,神圣的湖水更让他看清了今生的所求——不是一时成败,而是要确保灵魂的淬净与从容,如此,在漫长的旅程里必会收获一份厚重的果实。西藏是他此生的眷念之地,他的许多作品题材都来源于此。
回想大卫·妮尔对藏地的执着、刘曼卿进藏昭示怀远、今天的徐剑将军18次进藏,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痴心不改的执着,我想起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那一世》,那磕长头匍匐在山路的虔诚,以及念着玛尼石上诵经的真言。这部作品里,关于藏地的信息量是庞大的,以前,我仅仅知道文成公主入藏,从这部巨著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大卫·尼尔和她的《一个巴黎女人的拉萨历险记》;第一次知道了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梦想中的香巴拉王国;第一次知道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康藏轺征》;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赵尔丰;第一次对藏传佛教有了认识,还有灵山、灵地、灵湖及仓央嘉措的神秘……
不论是对宗教的虔诚也好,对文学的热爱也好,都是一种修行,一种执着,一种坚持。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们这些热爱文字、敬畏生命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喜欢在文字的王国里指挥着自己的千军万马,用的方块字排兵布阵,也都喜欢蘸着自己精神的膏血,记录下自己铁马冰河的豪迈和悲壮!至于说一路的患得患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决不会停步。文学需要这种至尊之境,如此清冷、寂寞,其修为可入不浮、不燥、不名、不利,只为自己内心真实写作,方可成经国文章,其肉身寂灭之后,唯有所写的方块字活着。
正是有了把功名利禄、沉浮毁誉都成身外之物的心态以及涅槃轮回都放下的安静,心中升腾的是一种敬畏,对神山圣湖、天地人心的敬畏之情,对西藏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的热爱,徐剑将军才三十年磨一剑,在《东方哈达》之后完成了生命之旅的涅槃《经幡》。
徐剑将军曾说过,文学的最高品质,“是宗教般的终极关怀,是悲天悯人,是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是描绘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间之暖、人道之高,是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对一草一木一物的景仰,对亲朋挚友的虔诚”。《经幡》正是这样一部具有“文学最高品质”的作品,徐剑将自己对西藏那片土地的一切情愫,都融入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