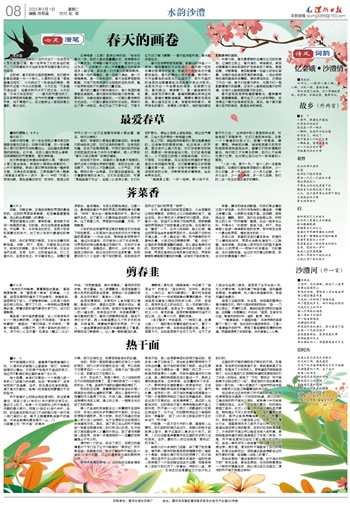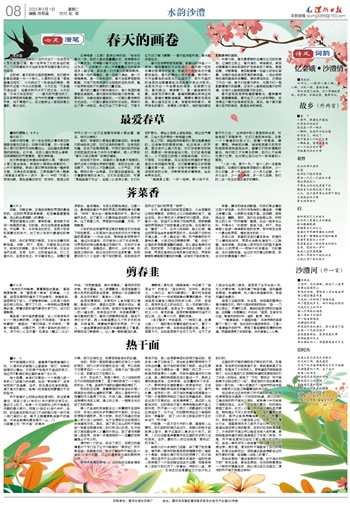■刘乔兰
早春,乍暖还寒,正是到田野挖荠菜的最佳时机。这时的荠菜非常鲜嫩,吃在嘴里慢慢咀嚼,舌尖就会漾起醉人的清香……
荠菜的香是淡淡的、素净的香,感觉胜于任何一种蔬菜的香。它的香,我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历经夏、秋、冬孕育生长的它,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爱吃的美味。
那时,我们称荠菜为野菜。它生长在镇郊的野地里。河畔、树下、菜地,只要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它的踪影。在冬天的豫中平原,它也会悄然生根、发芽、长叶。它的根呈白色,约二三厘米长,且根系发达;叶平铺在地上,因霜打雪凌缘故,呈深褐色,与泥土的颜色相近。立春一过,最早闻到春天气息的荠菜立即摆脱寒冬的羁绊,“呼呼”地长出一簇簇娇嫩的叶片,展示出盎然生机,成了春天人们最早品尝到的大自然美味。过了早春二月,荠菜就开始抽薹、开花,不再鲜嫩。
少年的我在早春荠菜正嫩时常跟在奶奶后面下田挖野菜。从饥荒年代走过来的奶奶对于野地里的草都能一一叫出名来。哪种能食用哪种不能,通过比较鉴别,奶奶教我认识了许多种草。对荠菜的识辨主要是通过观察叶片。它的叶片有好多种形状,有锯齿状、圆叶状、尖叶状等。我能独立辨识后,就让年迈的奶奶在家歇着。我和要好的几个小姑娘一起下田挖野菜,而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她们的荠菜“老师”。
冬天,家里每日的咸菜豆腐汤、大白菜真的让我吃得腻烦,我常吃上几口就假装吃饱了,溜出去玩。我太想吃点儿新鲜的可口蔬菜。因此,春天一到,我迫不及待地下田挑荠菜,那新鲜碧绿的荠菜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主角。妈妈偶尔也会“奢侈”一下,买点儿肉剁碎,掺上切细、腌过的荠菜给全家做顿荠菜饺子。妈妈把下好的饺子端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饺子香味扑鼻,大家边吃边啧啧称赞:“香,好吃!”这是我家早春最温馨的画面,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那时我想,天天都能这样吃该多好啊!大多时候,荠菜还是被妈妈用来单炒或烧汤。荠菜的鲜嫩和清香搅动着我的味蕾,总有吃不够的感觉。
早春,镇郊的绿色田野里,村民们常会看到三四个穿花褂、扎两只羊角辫的小镇姑娘,手臂上挎着小篮,小铁锹放在篮子里,在田畴、坡地间出没、蹦跳。有时,她们也会抬起头来,听树枝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喧闹,也会一起学鸟尖叫,吓得鸟儿“扑棱棱”赶紧飞走。树下,则会响起小姑娘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那中间定会有一个最会挑荠菜、调皮活泼的我……
多年以后,家里的生活已富足有余,我离开了小镇来到城市,荠菜也由野生演变为人工种植。每年早春,我总能从菜市场农妇的篮子里寻觅到心仪的荠菜——那种外叶深褐色、内叶碧绿,生长在野地里,经过岁月打磨过的野菜,我会与它的清香撞个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