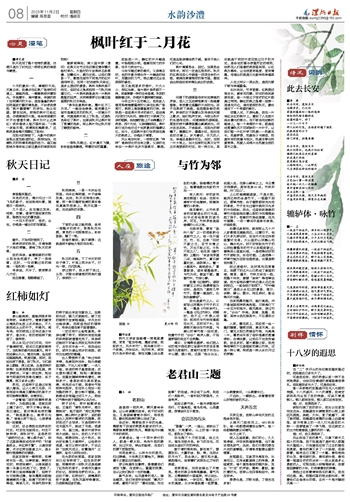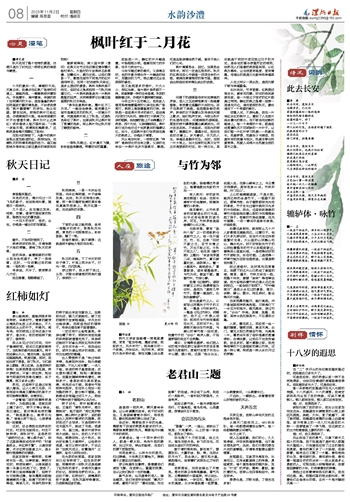■七 南
泰山路南段,道路两侧多种有柿树。早春时节,青黄的嫩芽从褐色的虬枝上点点萌出,不久就变成尖尖的叶子,听春风、闻鸟鸣。有的树活上百年还是少年君子,像水杉;有的树刚种下就老了,像柿树。
我从未见过它们开花,当叶子铺满树冠,枝间已见数枚青柿了。当和煦的春风变成夏风,柿子变成拳头大小,青皮光滑,坠在枝间摇摇晃晃,煞是可爱。那时,我站在树下想象,到了秋天,它们被涂上胭脂、穿上红装,会是怎样的惊艳?如果把想象往后延展,柿叶辞树后,只留一树红柿,宛如季节把谁的相思悬在晴空、系于晨雾,那又该多么美?
然而,这些柿子总是过早地被人摘走,让人心疼又无奈。只有那些长得高又藏得好的果子才有可能等到霜降,由青变红。
一家餐馆门前的那棵柿树是个例外。为招揽生意,老板在树上缠了彩灯,柿子才得以保全,现已橘红,更衬得其他树的黯淡。“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每每从树下走过,心底便涌起一股暖意。
这时,总会想起生我养我的村庄。村庄在龙城西北。村庄不缺柿树。深秋时节,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到了这里就得改成范宗尹的“村暗桑枝合,林红柿子繁”。从高空俯瞰,点点红柿如星星之火,是乡野村落难得的好景致。
我家东院有一棵柿树,和楝树长在一起,比楝树高。楝树开花时,柿树刚满叶,从侧面望去像一朵紫云托起了它,美极了。楝子果已经结得够稠了,但柿子比它结得还稠,每年霜降后都能摘满满两大筐。刚摘下的柿子涩得很,得烘几天。母亲先把半软的柿子挑出来放在窗台上,如果阳光好,晒几天就能吃。破了皮的硬柿子放麦秸堆里,半月左右也能烘熟。而那些完好的硬柿子,母亲会埋在麦子里慢慢烘。
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基地,母亲也藏了柿子。明明所有我知道的烘柿都被慢慢吃完了,母亲却还能时不时拿出两枚红彤彤的柿子,左手右手各一个,变戏法似的,或作为课业进步的奖励,或作为生病时的慰藉。
古人赞美柿子是“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里团酥。不比人间甘露”,一点儿不假。烘透的柿子晶莹剔透,皮比塑料膜还薄,轻轻一撕就能吃。我喜欢揭掉柿蒂吸着吃,绵甜多汁,像果冻却比果冻更丝滑。吸完皮也不破,再像吹气球那样吹起来,扣在手心宛如一枚完整的柿子,数分钟不塌陷。我就曾成功地骗过好几个人,把他们气得吹胡子瞪眼并以此为乐。
柿子好吃,柿叶能题诗临帖。王逢的“清秋书柿叶,落日赋桃花”、杨万里的“却忆吾庐野塘味,满山柿叶正堪书”,说的都是古人用柿叶题诗的风雅事。那时我还不会写诗,只是把柿叶夹在书里风干,就成了书签。郑虔诗、书、画三绝,曾采叶练字终有大成就。如今,我的儿子初习书法,颇费纸张。这个秋天,我决定收集几大箱柿叶,让他效仿郑虔,每日以柿叶练字,不求达到“如疾风送云,收霞推月”之境界,省点儿纸张也好。
在光阴的流转里,老家东院早已没有柿树了,但在我的梦里,那棵柿树一到秋天还是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仿佛作为童年的印记,深深烙在梦的尽头,永远忘不掉。红柿如灯,被褐黑的枝干挑着,在秋风里呼唤着我,为我照亮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