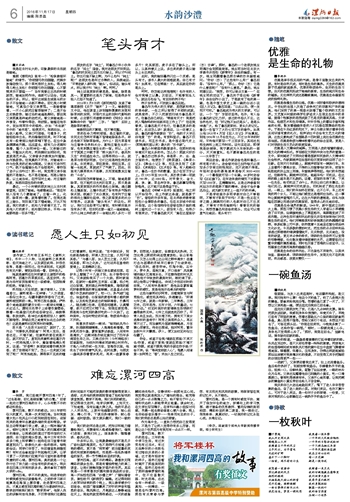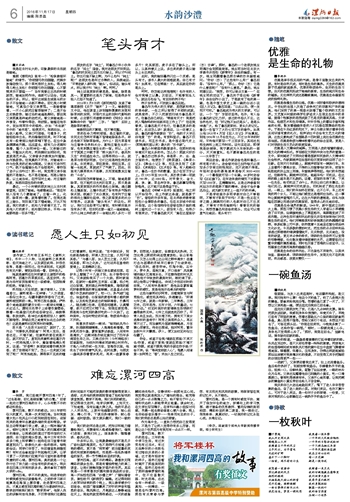■宋宗祧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印象最深的农活就是锄地。
豫剧《朝阳沟》里有一个“栓保教银环锄地”的情节:“你前腿弓你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使匀,那个草死苗好土发松。得儿哟得儿哟土发松!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当年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就想,锄地如同作诗。谁都可以说会,但真会的不多。所以,银环这城里生城里长的女孩子不会锄地一点都不稀奇。回忆我小时候锄地,可真没少受父亲责骂。一是锄着锄着,一不小心就把庄稼苗锄掉了;二是不会左右换姿势,锄过去的地遍是脚印。要说我父亲那真是种地的老把式。看父亲锄地是一种享受,咋看咋得劲,很舒服。锄握在他手中,犹如将军手中的银枪,亦如“书法家”手中的“地书笔”,轻便灵巧,挥洒自如,小鸟依人般乖。父亲口叼烟卷,弓着身子,把锄轻轻伸出去,然后稳稳拉回来,时不时地还有一股青烟从他的草帽下冒出,在空中袅袅娜娜地升腾。远远望去,颇有几分迷离和浪漫,整个人如同神仙一般。父亲锄过的地,平整如大花布,两排脚印如同印花,简直就是艺术品。父亲曾多次教我如何握锄,如何换姿势。但我真的不开窍,对锄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迟钝与隔阂。父亲无可奈何叹口气:既不会握锄头也不会掂笔杆,看你没了老子以后咋过!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手里握的不是锄头,也不是在锄地,而是以锄当笔,以土地当纸,在抒写对土地、对庄稼的热爱,挥洒田园生活的诗意。
最近,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润土从农村来看望我,说到了锄地。他感慨地说:“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愿锄地了。庄稼一种上,化肥、除草剂一撒,就等着收割了。但我还是扛上锄头,到田里不紧不慢地锄。不比不知道。我打的麦子,胚沟几乎都看不见了。而其他人打的麦子,胚沟要凹很多,平均一亩地要相差一百多斤哩。”
朋友的名字“润土”,同鲁迅少年小伙伴的名字“闰土”谐音。我对老朋友开玩笑说:“鲁迅的好友闰土因为五行缺土,所以才叫闰土。你五行里不缺土啊,为什么也叫‘润土’呢?”老朋友也是年过古稀的人,呆萌地说:“平常老家人都叫我‘锄头’。俗话说,锄头有水,所以我才叫‘润土’啊。呵呵。”
润土话里更深的意思是,锄地,除草是其一,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墒,但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2016年2月9日的《新民晚报》发表了褚建君教授《关于“锄禾”》一文。褚教授在文中说,他在课堂上讲到植物激素的发现和除草剂的发明,对现代农业的划时代影响的时候,必定要引用唐朝李绅的《悯农》诗并解释诗中的“锄禾”二字:“‘锄禾’实际上是除草的意思。”
褚教授说的不算错,但不够完整。
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是庄稼的天敌。农民无论怎样对草毫不留情地除恶务尽,却总也做不到斩草除根。为什么?因为草虽有与庄稼争夺养料水分、影响庄稼生长的一面,也有刺激庄稼生长的一面。所以,上天才于冥冥之中赋予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旺盛生命力。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草与苗同宗同族,它们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农民常说,草旺欺苗,苗旺压草。庄稼一长起来,草就成不了气候了。因此,田里有几棵草根本不是事,反而更能激发庄稼的“斗志”。
再回到怎样看锄地上。不错,锄地是要除草,但不能把目光死盯在草上,那只是表象。其更深层次的作用是松土保墒。通过翻松土壤表面,土壤中形成了含有很多气隙的保水层,既减少了水分蒸发,也有利于庄稼的根向土壤深处延伸,使之获取更多的水分和营养。这就是“锄头有水”的说处。所以,我们过去经常可以看到,有时候田里并没有多少草,但农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锄地。
为什么润土种的麦子一亩能比别人多打一百多斤?究其原因,麦子多在了锄头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出来的麦子是从锄头上长出来的。
此时,我的脑际蓦然闪出一个灵感:笔头有才。读书人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有才吗?如果有,它在哪里?才,其实就在你的笔头上。
呵呵,你怎能这样推理呢?也许有的人会对我嗤之以鼻。反驳说,不能看到鸟儿飞,就说马也会飞。有实际的例子吗?
例子当然有。不妨就从鲁迅说起。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一生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成果斐然,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为鲁迅是天才。但鲁迅自己却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但在我看来,说鲁迅是天才也行,但鲁迅更多的是笔才。此话怎么讲?就是说,从一定意义上讲,鲁迅的著作都源自“抄”,他的才大半出自他爱“抄”的笔。有资料显示,鲁迅不仅读书多,而且抄书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即晚清民国以来)最大的“抄书家”。
鲁迅小时候虽然酷爱读书,但那时的他毕竟买不起太多的书。怎么办?那就只好抄了。鲁迅抄过很多书。单是草、木、虫、鱼方面的书,他便抄了《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而且涉及到了《茶经》、《耒耜经》、《五木经》等。有人粗略估计,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至少在百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对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鲁迅都摹写得惟妙惟肖,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抄。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他之所以开始写作,走上作家这条道,就是源于“抄”。曾经的许多年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小佥事职务的鲁迅,住在北京城中的绍兴县馆。这个县馆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故没有人住,也很少有客来访,于是鲁迅就天天“寓在这屋里钞(抄)古碑”。那时,鲁迅的一个老朋友钱玄同偶尔会到那里做客。钱玄同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并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委。有一次,钱玄同翻着鲁迅那古碑的抄本疑惑地问:“你钞(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回答:“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最后,钱玄同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终于答应给《新青年》杂志创作小说了,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写道:“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可以说,一个“抄”字居功至伟。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的记忆力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当然也对,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笔头神通广大,给了鲁迅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
鲁迅一生留下了大约七百万字的著作。如果从他1918年4月写《狂人日记》开始算起,到他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不过18年半的时间,平均每天要写一千三百多字。其间还包括生病和上班工作时间。说句实在话,即便我是块钢铁,我宁愿成为火车铁轨的一部分,天天被重轧,也不愿做鲁迅先生的笔——太辛苦了!
再说老舍。著名作家老舍也是和鲁迅一样有笔才的人。老舍曾对自己创作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做出刚性规定,完不成绝不停笔。年轻时老舍的最高速率是每天3000~4000字,一个暑假就可写一个长篇。64岁时老舍写《正红旗下》,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要每天写1000字,且精雕细刻。正是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笔耕不辍的精神,老舍才会步鲁迅后尘,成为新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不是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对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有才耿耿于怀吗?不是一些正在文学之路上踽踽而行的人也都对自己不出灵感,不够有才很伤脑筋吗?看看农民的锄头,再想想鲁迅和老舍的笔头,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笔头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