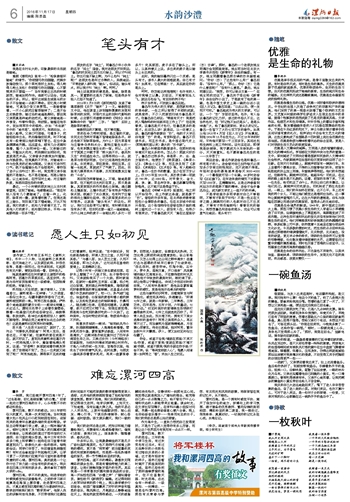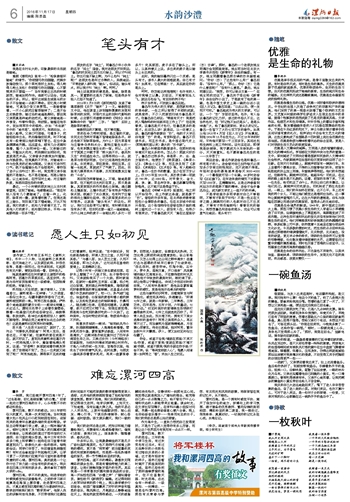■赵根蒂
读作家二月河帝王系列之《康熙大帝》,书中一个人物,比起康熙之英勇果敢、经天纬地之才,以及谋臣武将、奸佞忠良等,笔墨一掠而过。但书读到底,忆起那些有关片断,竟犹如惊鸿一瞥,回味良久。
她就是康熙在位时的蒙古土谢图汗的格格阿秀,因葛尔丹草原兵乱,逃至京师,先是与治河官员陈潢有过一段感情,但因陈潢的拒绝,有缘无份。
然而佳人天生丽质,兼才情照人,又体蕴香兰,康熙竟是一见钟情:“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阿秀已脱去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儿,腰间无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缨络,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流眄,洛神出水般艳丽惊人!康熙不禁暗想:异域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绝色!这就是康熙初见阿秀时的情景。
若只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就好了,又何必“何事秋风悲画扇”?阿秀入宫后,虽香还在,不增不减,但康熙的爱在或是不在,就不好说了。直到后来康熙亲征葛尔丹时,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摩挲着她满头秀发,说道:“好香啊!朕原就闻着你满身异香,进了宫倒闻不到了,怎么一出来就又闻到了呢?”阿秀抬起脸,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康熙,轻声说道:“宫中嫔妃多,到处都是脂粉香,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这句话用在皇帝的爱情上,实是精辟之至。
记得小时有一次随父亲去裴城拉煤,在驴车上颠簸了十几里才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就给我买了一个火烧,那时家里穷,在家时一般都吃玉米面、红薯,极少吃过白面馍,更别提这种烤得黄焦,隐现的葱花好像翡翠里的青丝般鲜嫩,还星星点点粘着少许芝麻的烧饼了。咬一口,热气破门溢出,油盐的香,白面里的麦香和着小葱的辣香,以及粒粒芝麻迸出的细碎清香,扑鼻而入,随后满口生津,在唇齿间缠绵,认真嚼着,都不忍把它们咽下去,到现在都觉得,那是我今生吃到的最好吃的一个火烧了。这种美味,与当时特定的环境、物质条件是分不开的。
我喜欢苏轼的一阙词:“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篙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是苏轼在黄州过了四年多谪居生活之后,又被迁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才高八斗的苏轼一生为官,宦海浮沉里,他失去了初时的意气风发。此时此景,与朋友一盏闲茶浮着雪沫乳花,再来一盘蓼茸春笋,回想起人生跌宕,纵朝堂风光热闹,又怎比得上眼前的闲适惬意放松,纵山珍海味,又怎么比得上这山间之野味清欢!连遭打击与屈辱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仕途荣枯,“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风流豪情终随大江滚滚东去,不在朝侍君的时光反而是他才华绽放的最美时刻,被贬谪了官,却让他得以宁静致远,诗词之中找回初时的自我。“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他品尝蓼茸篙笋时的感叹,更是他饱尽沧桑后的顿悟!
这些与康熙初识阿秀,后暂离深宫与阿秀独处,感觉极其相似。朱德庸说:“所谓七年之痒,就是一年新鲜,二年熟悉,三年乏味,四年思考,五年计划,六年蠢动,七年行动。”初见时美好的爱情被生活琐碎打磨得索然无味,七年之后就危机四伏了。平常人尚且如此,况日理万机、拥有天下美女选择权的皇帝乎!阿秀之美泯然众人,再正常不过了。而当康熙为国家殚精竭虑,为宫事心烦意乱,待走出围城,独对阿秀,繁华如秋叶片片飘落,伊人,便又如初见时似兰似麝了。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纵“等闲变却故人心”,惟愿人间诸爱一如阿秀之“香”,终如人生之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