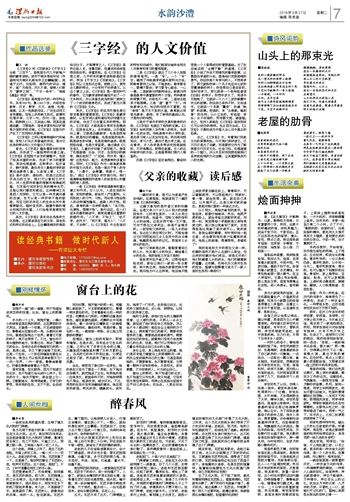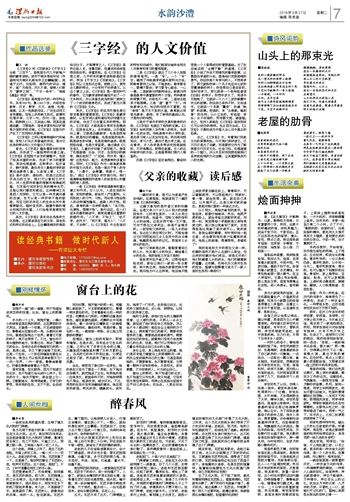■邢俊霞
面,《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从麦。解释极为简单,只有寥寥两个字,然而,由麦子的籽磨成的面,却极具魔力,成品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且不说形形色色的面饼、馒头、面包、糕点之类,单说面条就有挂面、龙须面、手擀面、牛肉拉面、油泼面、空心面、刀削面……
面条品种虽繁,我却独爱烩面。我自认为,挂面、龙须面像大家闺秀,中规中矩,气质沉稳,喜怒不形于色。烩面则像小家碧玉,古灵精怪,时常任性地耍一耍小脾气,在主人抻面时,它要么窄如细柳,要么宽如玉带,虽宽窄厚薄全无定性,却入味绵长,香而鲜美。
身为大家闺秀的挂面,多为机器批量生产,少温度而多僵硬,而身为小家碧玉的烩面是带着主人体温的,由着主人在手中千揉百搓,以至通体光滑、柔软无比。
烩面之所以会柔以绰态,媚以味蕾,那是因为它心中藏着爱呢。相传唐太宗李世民还未登基前,有年冬天,雪深风朔,李世民被敌军追赶,途中突患疾病,无力行走,只得下马寻求乡人庇护。
一对好心的母子,看他落难就收留了他,李世民病困交加、饥渴难耐,老婆婆就宰杀了自己家养的一只麋鹿,一边炖汤,一边取出一瓢白面,拿水搅拌,和成面团,想擀成面条为李世民充饥,可是,面虽和好,却来不及擀,因为担心后面的追兵,只好将面团草草拉抻了几下,形成条状下入肉汤锅中。
李世民吃了以后,仿佛人间第一美味,感觉味美汤鲜,吃得那叫一个过瘾,饭饱肚圆、大汗淋漓,不由得病势去了大半,精神大振。李世民登基后,虽遍尝山珍海味,但老婆婆的面汤还是让他魂牵梦绕,难以忘怀。为了报答老婆婆母子的救命之恩,他令人寻访,厚赏重赐。并命御厨向老婆婆拜师学艺,后经御厨改良,将麋鹿改为山羊炖汤,赐名羊肉烩面。后传艺民间,历经数代仍长盛不衰。使无数的食客在烩面的滋养中,掬一捧光阴,与时间同行,在岁月的路口静待花开。
我虽然厨艺不精,但所做烩面还是上得桌面的,是我待客的保留节目,只是做起来过程较为繁琐:先取高筋白面,兑入一小勺盐增加韧度,然后用水和成软软的面团,反复揉搓,使其筋韧,放置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用漯河话说叫醒面,仿佛面睡着了,静静地放一会,慢慢地等它醒过来。醒十分、二十分钟后再重新揉搓,然后再醒,等到面团软韧、表面发亮时再擀成面坯子,上面抹上植物油或者淀粉,一片片码好,用保鲜膜覆上备用。汤用羊肉、羊骨一起至少煮二个小时,少了不行,“豫剧的腔、烩面的汤”,汤是烩面的精华,要先用大火滚开再用文火慢煲,直到煲出来的汤浓白浓白,牛奶一样,汤才算煲好了。
羊肉汤煲好,开始做面,双手捏住面坯的两端,上下甩动、左右拉抻,即成长长的薄条。喜欢吃窄的,一分三条或四条,喜欢吃宽的,从中间一分为二,喜欢吃筋度高、厚点的,也可以整片下到熬好的汤里。煮面时,放上海带丝、豆腐丝、粉条,还可以放鹌鹑蛋。上桌时再点缀香菜、辣椒油、糖蒜,入口软滑筋道、舌齿生香。
烩面,作为一种吃食,在历代的传承中,渐渐背负了一种责任,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一种梦里乡愁,这恐怕是李世民当初万万想不到的。
那年,在外工作多年的同学回漯,穿西装,系领带,行为举止极为绅士。为尽地主之谊,我安排了一家高档酒店,然而,同学言语间只对烩面情有独钟,大有不吃不快之势。无奈之下,退掉早已订好的酒店,我把他领到烩面馆,刚一进店:“老板,一碗砂锅羊汤烩面,要大碗!”那一嗓子,仿佛梁山好汉下山一般,高嗓大调,真出乎我的意料。忍住好笑,我点上三荤三素小菜搭配烩面,又特意买来一盘上好的牛肉用来佐酒。
等面的间隙,我们边吃菜边聊天,聊上学时的趣事,聊双方工作的近况,话题投机,气氛融洽,一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场景。然而,面刚一落桌,同学立刻两眼放光,犹如天雷勾动地火,吃面的激情瞬间达到顶峰,一发而不可抑制,使得画风突变,同学伸筷就吃,哪管砂锅里的汤还在咕嘟着呢。正要低头吃之时,领带却垂进了碗中。同学一气之下,双手齐上,三拉二扯硬是把领带拽了下来。
同学吃得呼呼作响,额头上已然沁出密密的汗珠。听着响声,我在想:该是这萦绕梦里的响声把他带回故乡,来寻觅那一抹久违的乡音吧?
酒足饭饱,同学说:“烩面,不止饱肚腹之欲、口舌之感,更多的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人的乡愁。往事如酒,何以解忧?唯有烩面。”
一碗烩面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一种魂牵梦绕的牵挂,一种深入心扉的回忆。烩面抻抻,抻出家国情怀,抻出千般滋味、万种情怀,抻出舌尖上的记忆,犹如正月半的元宵、八月半的月饼,只要吃上一口,就能打开记忆的门,温润心底那悠长深远的回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