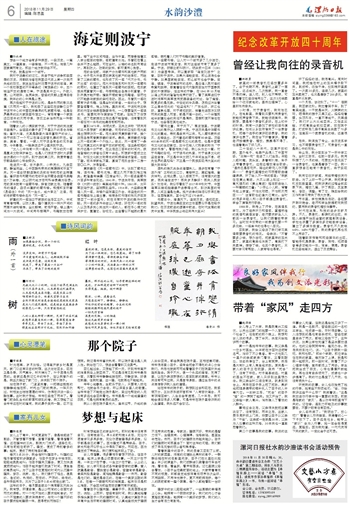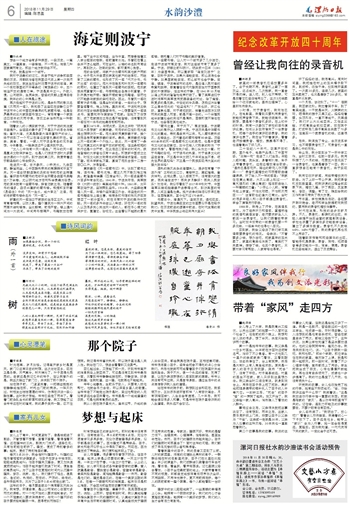■孙永辉
想去一个地方会有多种诱因,一段历史,一篇美文,一道美食,一缕牵挂,不一而足。倘若几种因素兼而有之,那这个地方就非去不可。
宁波,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我对宁波最初的记忆,来自于鸦片战争那段屈辱的历史,清朝统治者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败仗,就发生在当时归属宁波府的定海,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五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宁波是其中之一。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曾经的天朝上国满目疮痍,我年幼的心中满是义愤。
再次唤起对于宁波的认知,是余秋雨的散文名篇《风雨天一阁》,我知悉了这座现在安静伫立于宁波市中心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背后有着一个家族近四百年的风雨守候,惊叹之余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向往。
随着女儿的小姨安家宁波,对于宁波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当姐姐的妻子多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牵挂;喜欢大海,尤其是酷爱大海丰富物产的女儿,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海边安营扎寨的所在。省亲、美食、看阁,一家人对宁波各有各的无尽遐想,今年暑假,一路奔波近千公里来到宁波。
“文人心中均有一天一阁矣。”而今的天一阁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到宁波的第二天,我便带着近乎朝圣般的心情去探访。
走进天一阁,古木参天,小桥流水,九曲回廊,静谧清幽,心中因酷热带来的焦躁瞬间平复下来。天一阁由明朝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喜好读书和藏书的范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范钦原本就有一座藏书楼,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须兴建新的藏书楼。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范钦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新建的天一阁独立于家族的生活区之外,中间有高墙相隔,以防火患。整个建筑为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开窗。楼上通六间为一大统间,中间用书橱隔开,书籍就放在橱里。楼下当中三间相连,当作中堂,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题写的楹联,阁前建有水池。尽管现在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可在当时,从楼的命名到布局设计,再到防火、防潮的安排,都可谓用心良苦。
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的藏书,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范氏家族共同掌管天一阁,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子孙齐集方能开橱;擅自开橱或借出书籍者,惩罚他们不能参与家族的祭祀活动。因此,尽管天一阁收藏有许多书籍,但是当时的学者、一般的士子,想要登阁看书,难上加难。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想到,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没有看到天一阁任何一本书的她最后郁郁而终。
直到1673年,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范光燮钦佩黄宗羲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自此,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严苛,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请求登阁,也碰了壁。版本学家赵万里,宴请了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〇二户,方得登阁。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有去无还。1841年,宁波失守后,英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盗书。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出售,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了一部分图书,却在日军对宁波的轰炸中焚毁。天一阁的多舛命运让人唏嘘,好在天一阁的后人以及很多关心关注天一阁的人,都在尽心竭力的保护它、重建它、珍视它。这座看似不起眼的黑木阁楼,寄托着人们对于书籍的美好憧憬。
一座藏书楼,让人对一个城市多了几分迷恋,走进宁波城市展览馆,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了解。宁波,明朝之前叫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所以重新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府。如果大海能安定,那么波浪也会宁静。如果国家能安定,那么城市也会宁静。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的名称,是沿海人民对海的希冀和崇拜,寄寓着世世代代黎民百姓对于国泰民安的朴素期盼,但这样的宁静,在1841年10月被从海上而来的隆隆枪炮声打破了。看了英军进犯宁波时清军和英军使用武器装备的对比,除了痛楚,我更多的是无奈。中世纪的冷兵器,怎抵过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船坚炮利”?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挟着先进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来临不是偶然,屈辱即使不降临在宁波,也会落在其他地方。
“藏书之富,甲于天下。”展览馆里,宁波藏书文化的展示让人眼前一亮。宁波历来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地,特别是自宋代以来,私人藏书蔚然成风,名楼迭出,历代著名的藏书楼有80余座。历经400余年的天一阁是藏书文化的典范,也是中国藏书文化的生动象征,如今已被人们形象的称为“宁波的书房”。看罢相关介绍,我心头为之一震:对于书籍的珍视,对于读书的热爱,对于自身文化的坚定自信,不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间生生不息、领先世界的奥秘吗?不正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资本吗?
湿热的晚风夹杂点海腥味儿,漫步在有着“宁波外滩”之称的三江口,高楼林立,霓虹璀璨,喜庆祥和。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没有强大的国家,哪来海定波宁?哪来岁月静好?哪来人民安乐?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2017年中秋时节,中国海军三艘舰艇缓缓开进泰晤士河,到访英国的情景。人间正道是沧桑。鸦片战争的硝烟似乎早已散尽,但屈指算来,至今也不过170余年。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追溯历史,透视现实,眺望未来,宁波沧桑巨变的立体图景似乎是在昭示我们: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