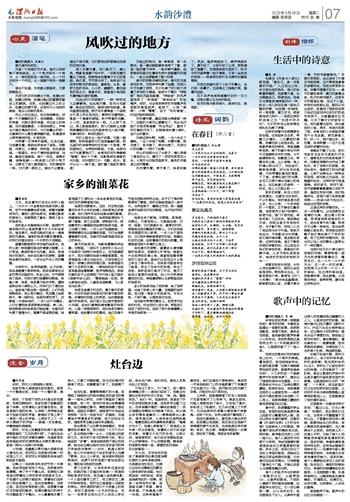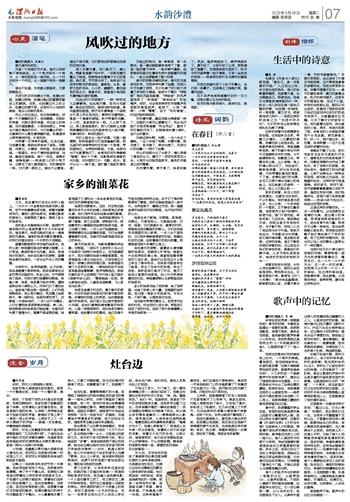■愚 停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道:“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过而立之年,终日被生活的洪流、烟火的俗事裹挟缠身,我疲惫不堪,也无暇爱自己。即便如此,我每天也要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出一点儿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喝一杯咖啡、听一首老歌、看几页书,或信笔写诗三两行……我把这样的时刻称之为“生活中的月光”。它们的存在让我觉得生活处处充满了诗意。
这样的诗意并非都需要自我创造,还有些来自自然。带着三分惺忪、二分朦胧的清晨,我躺在床上欲起未起,忽闻数声春鸟的啼鸣,简直是醒神良药。楼下的紫叶李似乎昨天还是满树点状的花苞,今天竟满树粉花,有飘雪之状,带着空灵之感,让人惊艳。地上的蒲公英也开了,花如金币,傲娇地举着,时光在花间温情。天空带着玫瑰色的黄昏。下了班,我等红绿灯的间隙,忽见几只燕子停泊在路口的电线上,如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时间,我心上已起乡愁……
更多的诗意,来自心灵的由衷满足。这满足无关名利,不以价值论,有时甚至是无用之功、无心之举。一千多年前的一个雪夜,王子猷忽忆戴安道,连夜乘舟从绍兴到嵊州,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率性何其!几百年后,雪夜换成月夜,苏轼去承天寺寻张怀民。与子猷不同,苏张二人见了面且相与步于中庭。那夜月色如水,竹柏影如水中荇藻。他们肩并肩走着,甚至都未言语。这样的夜晚,是王子猷和苏轼的诗意时刻。这让我总为他们的率性动容,就像他们手捧月亮,从岁月深处悠悠走来,给迷茫的我送来皎皎月光……
诗意时刻有长有短,长则从浮生偷得半日,短则从俗务抽身须臾。哪怕身未及出,只够思想走个神。唐寅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一事,竹时寺里看梅花。”尽管日常琐碎,他还是寻了片隙去寺里赏梅。这片隙便是唐寅的诗意时刻。而我也常常效仿他,沿着河堤看尽百花——春天的樱杏海棠、夏天的紫薇合欢、秋天的栾花桂子,还有冬天的雪里红梅。在这个小城,所有的花我都认识,都可以叫出名字。我曾用了很多时间努力走近这些花并记住它们的名字和样子,也曾翻遍手边书籍,只为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因为爱着这些花,我也爱我的小城。周末,母亲为我熬了粥,淡黄色的小米粥里浮着两个白色汤圆,黑芝麻馅儿的。咬一口,甜汁溢出来。我吃着,母亲笑着——这不正是生活的诗意所在吗?
每晚孩子睡了以后,我忙完家务会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橘黄色的光芒柔柔地洒下来,四散到周围的光芒成了颗粒状,有了老照片的质感。我沐浴其中,像躲进了时光的隧道,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神圣的东西,或可称之为圣洁。在喧嚣的世间,这样的安宁很是难得。有时读书,有时不读,空气里静静飘散着春之花的气息。逢老友发来问候,我们轻聊两句,话语不咸不淡却饱满纯粹——我说今夜月色如水,她说正好用来安眠。
正是这样的诗意时刻,一点一点发着光,让生活焕发出温情的光亮、透出微小的幸福。即使直面那些惨淡的日子,我也有勇气和力量;即使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我也依然能够从容淡然;即使被生活的鞭子抽打得如停不下来的陀螺,有了这样的诗意时刻,我也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旋转出不一样的舞步。
当我们终日为六便士奔忙劳碌的时候,需要制造一些月光和诗意来慰藉自己、犒劳自己。这一小片一小片的月光、这一点一点的诗意,如同烟火之外的一个又一个的驿站。在这样的驿站里,我稍事休憩、洗去疲惫,从而焕发神采、披荆斩棘,最终抵达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