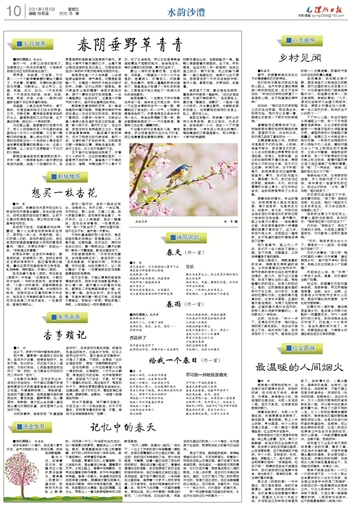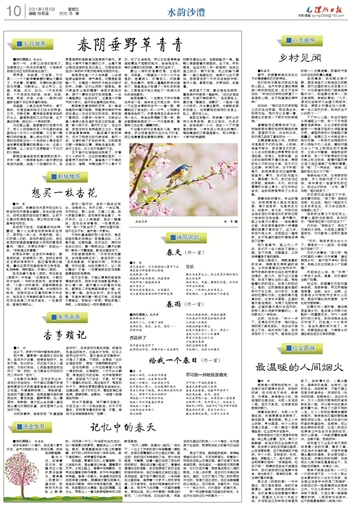■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还是个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少年,闲来无事,我来到田野踏青。
春光大好。我骑着自行车,顺着河边小路欣赏沿途春光。青得逼人的麦田一望无际,和煦的风吹在脸上暖暖的,河两岸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灿烂绽放,如一簇簇黄云般飘荡,看起来让人心旷神怡。野花、野草星星般在大地上眨着眼睛,时不时从树林中传来一阵阵鸟鸣,虽不是很美妙,却带着自然韵律。
田地里,零星可见农人忙着春耕,风儿轻轻吹来,混合着泥土味道,裹着草木芬芳。乡间土路上,春意中写满勤劳,无声述说着春日耕作情景,安宁中洋溢着收获希望。难得一日春光,我追随河流的足迹探寻春之踪影,眼睛面对着无限春光,有些目不暇接,呼吸中有狗尾巴草、紫云英、车前草的淡淡清香;路边的青蒿、马兰头、荠菜让人一看见就想起美味可口的野菜春卷。
“郊外人烟稀,挑春光一担归。”阳光下,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背靠着一棵杨树,在被浅草覆盖的乡村土路边打盹。路过时,我的自行车响惊扰了他,老大爷站起身,弓着腰,拄着一截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拐杖,慢悠悠沿着小路走了。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身影,我忽地想起了我已去世的姥爷和爷爷。他们也曾在这样的土路上来来回回,留下数不清的足迹,一年四季在土里刨食,维持着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日子虽艰辛,但他们用稳健的步子丈量人生,用尽气力生存着,一天都未曾懈怠。想到这些,我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那些在时光里远行的亲人一个个离去,终究是再不会回来,即使现在故乡的春天已经到来。
再往下游走,路就越来越窄,窄得勉强能行自行车。于河流拐弯处,我看到一树桃花在地头开得正艳,禁不住停下车来细细观赏。桃花盛放,一副地老天荒的模样,它们兀自开着,即使是在荒无人烟的野地,少有人来欣赏,但它们仍开得这样绚烂。是的,它们不是为了别人的欣赏而开放的,而是为自己绽放,在这远离喧嚣的乡间陌上,在天地间,在春风中,开出一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春天来。
那一树在野地里兀自盛放的桃花,永远开放在我记忆中的春天……
■流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