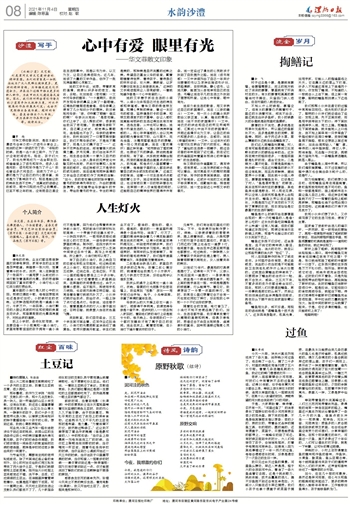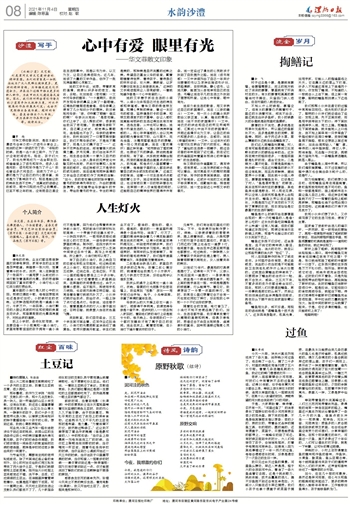■余 飞
村子过去是个寨,是寨就有寨墙。修寨墙需要土,挖土的地方就成了深深的寨壕,壕里就有了环绕村庄的水。有水的寨壕和高高的寨墙将村子围住,只留四门供人进出,住在村里的人就很安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寨墙没了。但有水的寨壕仍然围着村子,里边的水绕着村流,却流不出去,里边就生出许多鱼虾。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那里钓鱼摸虾。
寨壕的水不流动,最多就是在雨季补充些雨水,所以里边的鱼都长不大,且多是些野生的泥鳅、草鱼等。同时,由于两边多水草,草丛覆盖的水边就生出些鳝鱼来了。
我们这儿把鳝鱼叫黄鳝。村人很有可能是根据这像泥鳅却又比泥鳅长的家伙的颜色给命的名。这东西在南方的稻田很多,一是稻田里都是松软的泥,适合它生长。二是南方人喜欢吃鱼,只要是鱼就能大快朵颐——况且这叫鳝鱼的家伙不但没有乱刺,而且肉质鲜美,据说营养十分丰富,因此就十分招人待见。寨壕里有鳝鱼生长,应该是应了村人“鱼是草籽繁生”的断言。其实在那环绕村庄的寨壕里,其他鱼类也都是野生,村人司空见惯,所以没有人去探究那鱼是怎么出现并生长的。鳝鱼之所以在这里生长,大概是因为这不流动的水下沉积了厚厚的淤泥,而淤泥恰恰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吧!
鳝鱼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寨壕里出现的?第一次吃鳝鱼的人是谁?怎么吃的?这长长的鱼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没有人知道,但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好吃,即便没有油只在铁锅上炕熟,那香气也能让我们的口水流到下巴上。
鳝鱼这东西不仅好吃,还全身是宝。且不说它的美味诱人垂涎,单单那止血、消炎的功效,就足以让那些所谓的消炎药“脸红”了。
村人在田里耕作时免不了破皮受伤。乡村医疗条件有限,像这些破皮、流血的小伤当时是不可能跑到卫生院包扎或作什么消炎处理的。这就显出黄鳝血的神奇来了:只要把涂了鳝血的纸往伤口一贴,就不会发炎、感染。三五天下来,不管多深的皮外伤都会愈合如初。因此,那时人们只要逮到鳝鱼,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头剁下,然后让那汩汩淌出的血涂满整张旧报纸,再在日头下晒干后放到家里珍藏以备用。
鳝鱼用处多,却不好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逮鳝鱼是个技术活儿”。这东西浑身黏液,极其光滑,如用手抓,它能从人的指缝里逃之夭夭。它在靠水边的草丛下打洞,许多人不知道这洞有上下连通两个洞口。你发现了鳝洞,不知道的人一般就会从上往下掏,但上面一有动静,聪明的鳝鱼即刻便从下边逃跑了。
我们那帮小伙伴在逮它的过程中常常铩羽而归。但失败的次数多了,聪明的小伙伴们就总结出了经验:发现上洞,先不正面突破,而是用手探寻到水下的口;待下面找准再伸手入洞,用力上捅。那鳝鱼见下面被偷袭,就本能地从上口逃生,岂不知上面早有一只手弯曲了手指成钳状在洞口等着。受惊的鳝鱼慌不择路,根本没想到上面还有埋伏,如此出洞即钻入“魔”掌。等待的人将中指拱起,待它入手,即将食指、无名指一齐收紧,再顺其力猛向外甩,一条鳝鱼便活蹦乱跳落入草丛。
由于鳝鱼是从洞中所得,所以我们通称掏黄鳝。只不过在掏的过程中偶尔也会掏出条水蛇什么的,很是吓人。
因为怕掏着蛇,我们就想办法去钓。但那鳝鱼经常在洞里窝着,像钓鱼那般用钩钓是不可行的。鱼钩一般都是弯的,挂上蚯蚓吊在水里让鱼儿自己上钩。但这样去钓鳝鱼就不行了——弯着的鱼钩上蚯蚓再新鲜,那鳝鱼也绝不会爬出洞口自动吞钩。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另觅良方了。
我和小伙伴们想了许久,又仔细观察了它的生活习性后,便有了主意。
回家偷了娘做针线活儿的缝衣针,一折两段,取一段用线拦腰拴了,再用一根麦秸秆将挂了蚯蚓的断针穿住,而线则顺秸秆捏在手里,那鱼饵裹着的钓具就是直钩——直钩钓鱼的传说,就这样实现了。
断针上挂了蚯蚓,再把秸秆带线轻轻捣入洞口。洞中的鳝鱼见有美食送到嘴边岂有不吃之理?于是,张口就将那挂了蚯蚓的半截断针一口吞下。这东西只要咬住东西是万万不松口的。刚开始,断针虽被它咬住,却尚未被完全吞进肚里。这时我们并不着急,只是先轻轻把那带线的秸秆抽出,再轻抽拴了断针的线。此时的鳝鱼已将断针吞进口中,越是拉线,它越怕到口的食物再被夺走,就越往下咽。待我们觉得那半截断针已被鳝鱼完全吞进肚里,手中拉线的力量就猛然加大,拴在中间的断针立马就横了起来。于是,任它多滑的鳝鱼,也只能被钓上来了!
咱聪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