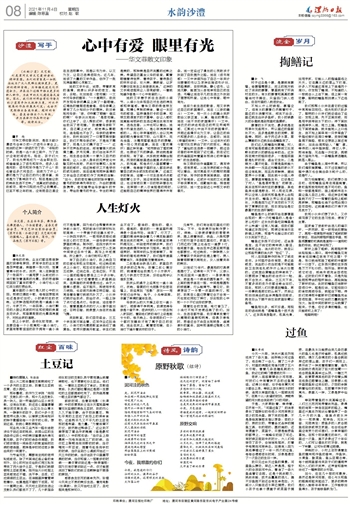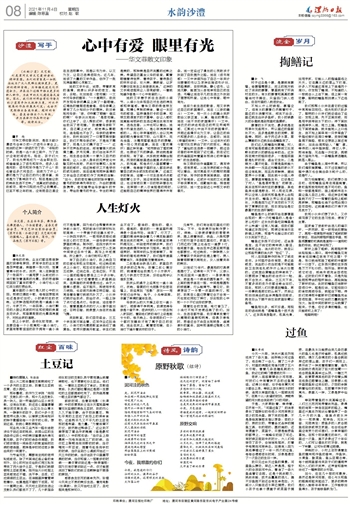个人简介
华文菲,本名华书芬,舞阳县北舞渡镇人,个体经营者,省杂文学会会员、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喜欢读书、写作,作品散见《漯河日报》等。
■华文菲
停电的夜晚,业主们都在微信群里打探停电原因,家有学生的业主更是怨声载道。黑暗像一张大网,笼罩着寒冷的冬夜。突然,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一盏用萝卜头做成的小油灯散发着温柔的光晕。我的思绪瞬间回到了童年的巷子,小油灯也从记忆深处被打捞出来。
童年里的小油灯是儿时心中的太阳。即使已隔数十载,每每回想起来也还是亲切如初。小时候村庄的夜晚,让夜鲜活起来的就是一盏盏小油灯。千家万户,一年四季,小油灯颤动的火苗让孤寂的村庄和低矮的房屋生动许多,那昏黄微弱的光晕洒满屋子,衬托出家的温暖。
我上小学时,条件比较艰苦,学生要自备一个小板凳和一盏小油灯。家里有哥哥姐姐的孩子拥有一盏小油灯不是难事,因为他们会帮着弟弟妹妹做小油灯。那时做油灯的原材料比较简单:一个带盖子的空墨水瓶子,一小块四方铁片,一根用铁皮卷成细长空心的灯芯支架,一缕母亲针线簸箩里的棉线。制作时,在四方铁片中间钻个小孔,然后把棉线灯芯从支架中间穿过去半寸高,再加上半瓶煤油,拧上盖子,小油灯就可以用了。
有了自己的小油灯,我上晚自习的态度也积极主动起来。吃过晚饭就点上小油灯,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边说边走,边走边玩,不足一公里的路程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钟。一盏盏小油灯扭着腰肢从家里跳出来,在黑暗的夜间慢慢划过。由于火苗瘦小虚弱,经不起风,即使用手极力遮挡,也总被风刮得忽明忽暗,经常走着走着灯就被风扑灭了,小伙伴们就你给我点、我给你点,一路上除了点灯还是点灯。母亲说,站在巷子口,看着星星点点的灯火从巷子里划过,忽明忽暗,就像萤火虫在夜色里飞舞。
来到教室,我们自动组合,三五个学生面对面坐着,边写作业边玩油灯。小油灯的光晕把教室涂染成了橘黄色。老师只要离开教室,学生们就坐不住了,借油的、借捻的、借火的、借笔的、借纸的……教室里热闹得像个自由市场。油洒了、灯灭了,浓重的煤油味掺杂着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说笑打闹声,让寒冷的教室变得热闹无比。听到老师的脚步声,我们就快速装模作样地学习起来。晚自习结束时,有同学的头发被燎糊了,有同学的眉毛被烤焦了,我们指甲盖里藏着油灰,浑身都散发着煤油味。
二叔是做白铁活儿的,家里自然很多铁的边角料。我看二叔心情好时,就缠着他给我剪几个小方铁片、做几个铁皮灯芯支架,好送给同学以维系友情。
我床头的桌子上经常放一盏小油灯。夜晚,昏黄的灯光把影子投射在墙上,我经常玩“投影”游戏——用手变幻出手枪、兔子、小鸟等图案,丰富了单调的童年生活。
母亲床头的大木箱上总放一盏小油灯,被擦得干净明亮。我便觉得母亲是个爱干净、很讲究的人——我去别人家玩时,看到他们家的油灯上总是脏兮兮的。每天晚上,母亲把我们一个个都打发睡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她坐在床上,戴着老花镜,在小油灯下缝补着贫穷的日子。
元宵节,我们有往祖坟里送灯的习俗。下午,母亲便开始制作萝卜灯。傍晚,父亲便领着我的哥哥弟弟,提上装着烧纸、供品、火柴和萝卜灯的竹篮子去祖坟里送灯。家里大门两边的门墩上也各放一盏萝卜灯,每间屋子里、每台压井边甚至厕所里也都要放。吃过晚饭,一群群男人女人带着孩子来到护庄堤上看灯。男人抽着烟聊着天南地北,女人说着来年的美好。
20世纪70年代,最高档的灯具便是提灯了。记得有一天下午,父亲从外地买回来一盏提灯:一身铁骨刚架,底座是一个装油的圆形盒子,和上面的提手连在一起,中间是椭圆形的玻璃罩,灯头能调节。看见它,我便想到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灯。那时,我常在心里幻想着它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阿拉丁神灯,好实现我心中那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灯普及了,小油灯不知不觉便远离了我们。如今,生活在都市里,我尽情享受着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明亮,但偶尔停电时,思绪还会不由自主地转身,追溯淳朴的童年,回味那温暖过稚嫩心灵的小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