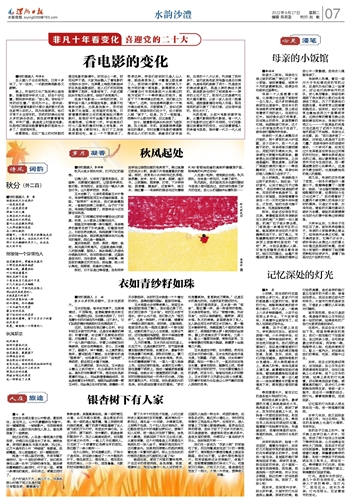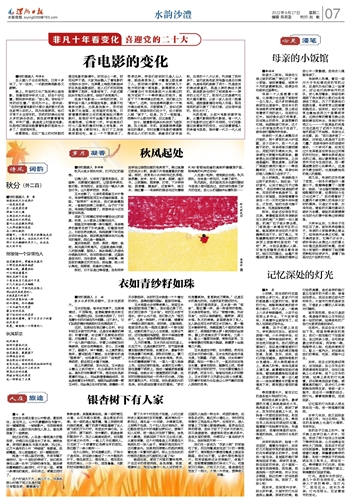■韩娟娟
我读大二那年,母亲在父亲上班的机械厂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每到寒暑假,结束半个月的家教兼职后,我便会匆匆赶来这里帮忙。
母亲一个人经营着小饭馆,父亲偶尔也会趁下班招呼一会儿客人,但大多时候他都奔波在出差途中。老实本分的母亲虽然非常瘦弱,身上却总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永远不觉得累。田间地头的劳作、家庭琐事的忙碌,她都能游刃有余。这个小小的饭馆自然也不在话下,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的一天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那个煮饭的炭火炉很重,至少百余斤,我一个人是搬不动的,母亲却每日搬进搬出。用鼓风机引燃炭火后,母亲便在大铁锅中轻煮面条,翻滚捞出后还要晾凉拌油,之后准备酱料、摆放桌椅,去机械厂院里打满两大桶水……等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母亲也剁好馅儿在擀皮儿包饺子了。
自小时候起,母亲就很少让我干家务活儿。她总说:“好好读书,以后才能让日子过得清闲。”我总觉得忙碌是她的使命,而我的使命就是学习。直到在小饭馆里,我亲眼看着母亲在一天一天的忙碌中年华逝去,才发觉,她的无怨无悔不是认命,而是坚强地活着。
那年,我家还没有在市区买房,寒暑假里我和母亲就挤在父亲机械厂大院的一间小屋里。机械厂位于城乡接合部,门前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公路,路面被来来往往的大货车碾得坑洼不平。到了晚上,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加上破旧的房顶上老鼠啃咬梁柱的“吱吱”声,令我总是难以入眠。可每当我辗转反侧去看母亲时,她已沉沉睡去,丝毫不受嘈杂的影响,那困倦的模样让我心中一阵酸楚。我有点儿佩服母亲了。
母亲待人热情,看见一些开大卡车拉煤送货的司机过来,总是先为他们端上一盆清水,好让他们洗净油污的双手,安心享用餐食。那些在桥洞底下卖水果的小贩们也和母亲成了朋友。为了不耽误他们招揽生意,母亲常常让我端着饭碗送去。回来时,他们也常常会塞给我两三个香蕉或苹果。这种对等的善意交换让我感到满足而快乐。母亲亦有怜悯之心——一个捡废品的流浪汉在这里吃了近两个月的面,每次都说下次给钱。母亲也从未在意,说:“我只是多做了一碗面,对有些人却是活下去的力量。”我被母亲朴实的话语所感动,一个学问不高、没有见过大世面甚至没有走出过河南的农村妇女,精神世界却是如此的辽阔。她以最简单直白的劳作方式与生活对话,用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处事待人,这是岁月教会她的,也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
那几年,母亲的双手布满了老茧,一到冬天便裂开一道道口子,粗糙得像覆了一层磨砂。她说:“未出嫁时曾摸过姥姥粗糙的手掌,没想到如今自己也这样了。”我仿佛看到了扎着两个麻花辫儿的母亲少女时的模样,只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曾经的天真烂漫早已被岁月收藏,曾经的柔弱臂膀也在时光打磨中抵得过惊涛骇浪。
大学毕业后,父母终于在市区买了房。前年弟弟结婚生子,母亲的小饭馆便停止营业了。但母亲并未停止忙碌,每天操持家务,忙得不亦乐乎。或许母亲从未想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类深刻的命题,我却在小饭馆的一隅看到了她用勤劳耕耘的如诗岁月,读懂了她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