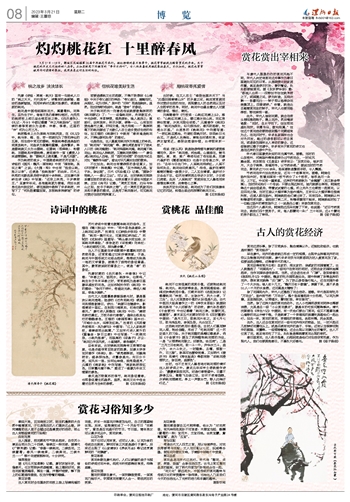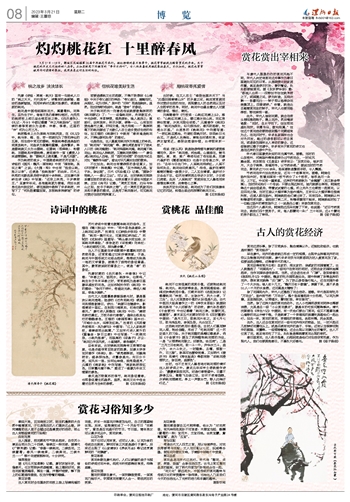3月17日~19日,郾城区龙城镇第26届中原桃花节举行。桃红柳绿的春日胜景中,桃花常常被视为踏青赏花的序曲。关于桃花的历史文化始终耐人品寻。正如苏轼笔下所描写的“争开不待叶”,古人向来喜欢用桃花象征春天,不仅如此,桃花也常常被用作对爱情的象征,或用来表达对生活的向往。
桃之故乡 泱泱悠长
先秦《诗经·周南·桃夭》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篇贺的是新婚、描绘的是新嫁娘,而用来映衬这喜庆场景的,便是绚丽的桃花。
桃花是中国传统园林花木,属蔷薇科,花单生,且先生于叶,每每天色仍春寒料峭时,光秃秃的桃树枝上却已呈含苞怒放之势。《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中都记载着“仲之月桃始华”,古时候的春季常被分为孟春、仲春、季春,这里的“仲”约为公历三月。
桃树整体上分为果桃与花桃两类,在《礼记》中,桃与李、梅、杏、枣一同被列为了祭祀神仙的五果,而生活中常见的碧桃、寿星桃等都是典型的观赏类桃木,花型多为复瓣和重瓣,品种繁多,单是碧桃就又分为白碧桃、红碧桃(即绛桃)、粉碧桃、花碧桃和洋碧桃等。秦观曾作一首《虞美人》来盛赞碧桃,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
作为桃树的故乡,中国栽培桃树的历史悠久。诗经的《国风·魏风·园有桃》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之说;《大雅·抑》中也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便是“投桃报李”的由来。汉代上林苑的无数名果异树中就有十余种桃,正如唐代李峤在诗《桃》中写道:“还欣上林苑,千岁奉君王。”至唐宋年间,各地植桃更为普遍,例如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便在庭院中栽种了许多桃树,并写下了“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城”的诗句。
借桃花喻美好生活
若要追溯桃文化的起源,不得不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夸父追日的神话:“夸父追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其中的“邓林”即是指桃林。显然,在古时候的传说中,桃是“救命”的象征。
关于桃花的另一则著名传说就要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如王维的《桃源行》中就有“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感叹。
也是因此,古人喜爱用桃花作为地理上的命名,如“桃花坞”“桃花庵”等。唐伯虎更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唐伯虎以桃花仙人自喻,用“老死花间酒”的生活方式去对比“鞠躬车马前”,暗含对平凡真实生活的歌咏。
不仅如此,桃花也有着辟邪的象征意义,如《齐民要术·种桃篇》中记载,“东方神桃九根,宜子孙,除凶祸”,汉代《风俗通义》记载,“腊除夕饰桃人……葵以卫凶”。可以说,古时候桃花既联系着百姓的安居乐业,也联系着太平盛世与国家兴衰。正如《尚书》记载,“周武王克商,归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这一周武王凯旋而归后和平景象的描述,正是用了桃花做衬,可见桃花对美好生活的特殊意义。
用桃花寄托爱情
古时候,在文人志士“修身治国齐天下”与“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矛盾之间,桃花常常被用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现着古人的自然观以及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同时,桃花中也蕴含着古人对爱情的象征、慨叹、寄托。
刘禹锡曾作《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感叹:“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元稹曾作《桃花》道:“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春风助肠断,吹落白衣裳。”白居易的《晚桃花》中则描写道:“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传说《钗头凤》就是陆游惋惜与唐婉的凄美感情而作,其中“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等词句成了传世经典。而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是千古传诵之作,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相传,崔护在清明踏青时邂逅一貌美少女,二人互生情愫,崔护对少女念念不忘,但次年清明再去寻访少女时,少女却已病逝。此后“人面桃花”常被后世文人墨客用来感慨世事无常、刻骨铭心之事。
泱泱历史长河流经,桃花成为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沉淀,构造出悠远而深厚的桃花文化。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