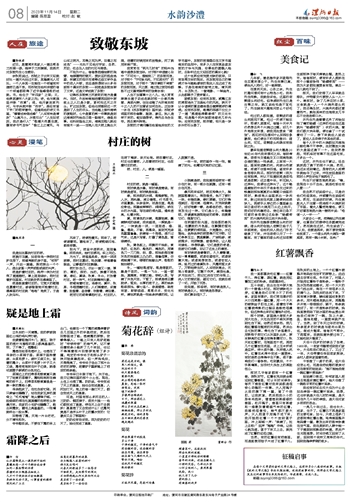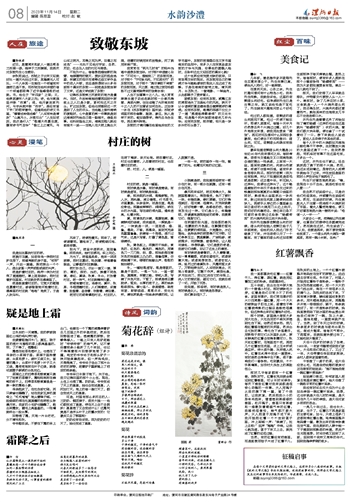■陈红卫
我一直都喜欢吃红薯——红薯干儿、烤红薯、蒸红薯,就连用红薯加工成的粉条,我都喜欢吃。
五十年前,我出生在中原大地的一个普通小村庄。那时候缺吃少穿,红薯是我们日常少不了的吃食。家里有煤炉,我们常在煤炉的火口四周摆一圈红薯,用一个大大的破铁盆子扣在上面。耐着性子等红薯被烤熟的过程总是感觉很漫长,但这样烤出来的红薯格外好吃。
那个时候,家里烧火做饭大多用大灶台,大灶台用的干柴灰烬落到灶台下面,依然还有余热。把几根红薯埋在锅底的灰烬里,然后出去忙别的事。等灶台下余温散尽,用铁钩子把它们从灰里扒出来,原本鲜亮的红薯会变得软糯可口。秋天收红薯时,在地里挖个坑,再挖几个红薯放在坑里,点上玉米秆或是豆秆。待火苗升腾、灰烬落入炕中,红薯在炙烤中变成一道美味。有时虽然会烤得半生不熟,却不影响我们一番争抢。吃到最后,个个手黑嘴黑,如农村大戏台上的黑脸包公。
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红薯窖。深秋时节,红薯收完后被全部运到红薯窖里,可以长时间保存。每次下窖拾红薯对我来说都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大人用绳子从我的腋下围一圈,留了个活扣,让我抓紧,然后把我小小的身体吊起来,慢慢落到黑漆漆的窖里。松开绳子,窖里只有黑暗和一堆散发着潮湿气味的红薯。我感觉很害怕,喘气都不敢大声。大人把篮子用绳子送下来,我开始把红薯一个个放到篮子里,冲上面喊一声:“装满了,拉上去吧!”回声“嗡嗡”作响,让我心跳加速。篮子下来又上去,就完成了红薯的运送过程。
当然,有的红薯没有进窖里,而是直接用刨子片成了红薯干儿。在秋后的土地上,一个个红薯片被整齐地码放在空旷的原野上,远远望去非常壮观。冬天来了,村里人开始用红薯粉子做粉条。一锅粉子加水加热做成糊状,用一个大大的汤勺舀出来,倒在一个有很多小孔的漏勺上。加热后的汤流下来,下面有清水接着,瞬间凝固成软软的条状。用木棍将其挑出来,再整整齐齐地一排排挂好、晒干,粉条就做好了。有一次做粉条的时候,妈妈直接把刚下到水里的粉丝捞出来给我们凉拌了一碗,加上大蒜、盐、香油和醋,一道美味就产生了。当然,到了冬天过年的时候,粉条更多的时候是与猪肉白菜为伍,做成大锅菜。每每天气转冷,下起雪来,我就知道快要过年了,又能吃到大锅菜了。
大伯十四岁的时候去了台湾。1988年,一封家书辗转送到我们家中,大伯和我们联系上了。又过了一年,大伯带着伯母回老家探亲,全村人都来家里看热闹。
午饭做了一桌子的菜,但大伯没怎么吃,而是走进低矮的厨房对正在做饭的姑姑说:“能不能给我做一碗红薯叶捞面条?”
姑姑满口答应,吩咐家里人赶紧去地里采摘红薯叶,给大伯做了一碗极平常的红薯叶面条。
我没有时间去问大伯为什么会如此牵挂一碗红薯叶面条,我想,这也许就是大伯儿时的味道,是大伯在外几十年的牵挂,是大伯对家乡浓浓的思念。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也长大、成家、生子了,红薯已不再是家里的主要吃食。如今,大街上很多门店都有烤红薯出售,电烤箱里整齐地码着一圈,散发出来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能一下子捕捉到那熟悉的味道,然后产生无限遐想。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那个贫穷又简单的年代,回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