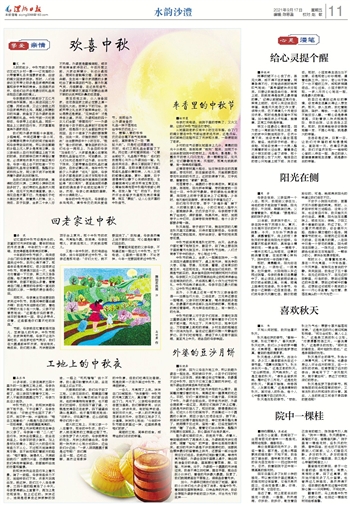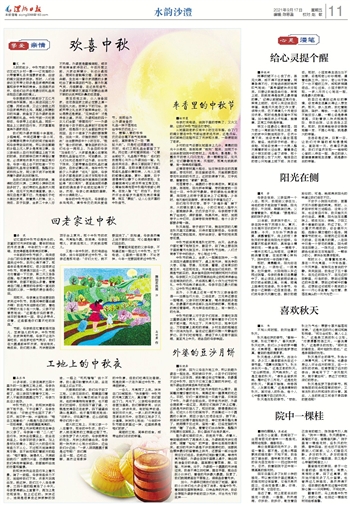■钮丽霞
母亲打来电话,说院子里的枣熟了,又大又甜,让我们中秋节回去打枣吃。
从城里到老家仅有半小时左右车程。出了门的闺女要在中秋节前给娘家送月饼,这是风俗。我们前晚已在超市买了月饼和水果,一早便赶到了老家。
乡村的空气总要比城里凉上几分,清晨的阳光十分柔和,渐渐地便“锐利”起来,如同万千丝线斜射到院中的枣树上,光是光,影是影。秋露未干的枣儿闪闪发光,像一颗颗宝石。无风时,它们静静地发亮;风起时,那亮光就跳跃着,有一种单纯的璀璨。
这棵老枣树高大粗壮,恰好种在我住的西屋窗前。枣花开时,我在窗前读书,风能把飘落的枣花吹到我的书页上。这时我便停下来,双手托腮,看着枣花“簌簌”飘落。
花落青枣小。扁圆的小枣长得很快,夏至后生甜。渐渐地,阳光拼命照耀,枣的甜度就一日胜过一日,中秋时节最甜。枣的颜色也由青变黄,向阳枝上的枣子甚至涂上了红胭脂。少年时,每天能吃到甜枣,便觉得日子幸福无边了。
我们用竹竿打枣,枣子“扑通扑通”掉下来,大的堪比婴儿拳头,小的仅有成人指甲大小,都脆甜多津。奶奶牙齿不好,母亲把枣子蒸熟了给她吃,绵软香甜,别具风味。有时,她把枣子从中切开,去掉枣核烧枣稀饭,每个小孩子都要多喝一碗。
秋风渐起,枣子被打下来,剩在树顶的几颗在秋风里兀自飘摇,只待夜雪压断枝条。母亲把干透的红枣捡起来,用针线穿好,春节时用来蒸枣花馍。
中秋节前后常常是秋忙时节。白天,各家各户都忙着下地掰玉米、割豆子,到了晚上要在院子里就着月光剥玉米。只有中秋节当晚,人们才肯停下手中的活计,专心地过个节。
中秋节的晚上,全家人一起围在院中,一张水泥四方桌摆在枣树下,桌上有月饼,有洗净的大枣、石榴、苹果、无花果、葡萄,还有煮好的嫩玉米、毛豆和花生。月饼是姑姑们送来的,苹果是节前买的,其余皆来自院中的果树和村外的田地。母亲把又大又红的苹果挑出来让我和弟弟拿给住在南院的奶奶,然后再私藏几个作为过节的节礼,中秋节当晚才拿出来。母亲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中秋节过得丰盛。
此外,小方桌上还有一瓶专为父亲准备的酒——如果恰巧大伯、二伯在家,三兄弟还要在一起喝酒。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喝点酒话就多起来。我最喜欢他讲在部队当兵时候的事,那是他的美好青春呵。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有一种动人的光泽。
中秋节的意义对于孩子们而言,尽情吃东西之重要远高于赏月,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们对月就不感兴趣。月光之下,天净无片云,地净无纤尘,万物都罩上柔和的滤镜,乡村生活的粗糙在那一刻消失殆尽,留在记忆里的只剩一片静谧的梦幻。孩子们吃饱喝足,便结了伴儿在巷子里玩闹,直至月上中天,被各自的母亲唤回。